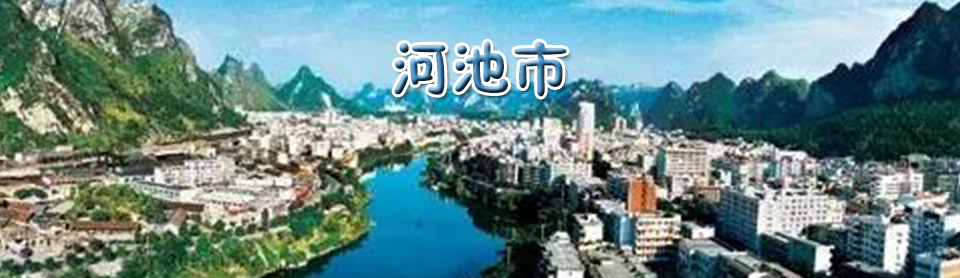畅春园兴衰的历史地理考察
“三山五园”是清代北京西郊著名的皇家园林。所谓“三山”,指的是玉泉山、香山、万寿山;“五园”一般是指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圆明园和畅春园。作为“三山五园”中较早兴起的园林,畅春园遗址现为北京大学所有,而其园林则早已不存。今天虽已无法再现畅春园当时的景观,但对于它的研究对了解京西园林发展史乃至清代历史仍具有重要意义。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畅春园兴衰原因进行探讨的不乏其人,但较少专门论述。张宝章的《畅春园记盛》一书是专以畅春园为题的一部著作,该书以畅春园的兴建、使用、毁弃为线索,站在康熙帝的历史维度,厘清畅春园的前后脉络。书中对畅春园选址海淀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刻和全面的分析,认为康熙帝选址海淀修建畅春园的原因有四,一是此地自然山水条件优越,有得天独厚的造园条件;二是地理位置适宜,距离京城近;三是历史人文环境良好;四是有明朝李伟修建的清华园为基础,可以事半功倍。此外,其他一些有关三山五园的文章及著作中对畅春园也有所涉及。尹钧科主编,魏开肇著《五园三山》一书先是对五园三山的历史作了总体概述,其中有专门一节介绍清代五园三山之兴衰,之后又分别对各个园林加以介绍。其中,对畅春园的东、中、西三路及西花园四部分专门辟有一章进行叙述。但无论是总体性的概述还是分别叙述,都侧重于对园林的发展历史及景观进行介绍,对畅春园兴衰原因尤其是兴建原因的探讨则较少涉及。侯仁之先生所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一书中收录了关于北京城的有关文章。其中,《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一文中,在探讨海淀附近园林的开辟与发展时,提到畅春园是在清华园的基础上建成的,而清华园之得以兴建正是得益于巴沟低地所处的地形、水源及其美景。其另一文《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中认为,清代“三山五园”的建设与河湖水系的开发和利用关系密切。此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书中在探讨明清时期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时也提到了清代对北京西北郊园林的开发。与前述二文相似,亦是侧重地理条件的因素。文章方面,张宝章《康熙年间的海淀园林》继承了其书《畅春园记盛》中的观点。岳升阳《海淀环境与园林建设》继承并发展了侯仁之先生的观点,对海淀地区的自然景观作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回顾了海淀园林的兴建历史,亦强调了海淀的环境优势以及已有的建园基础。阙镇清《再失一城——北京西北郊皇家园林集群:三山五园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没落》—文梳理了三山五园的基本脉络,对其形成的自然条件及兴废、整体格局等作了分析,其中对自然条件的分析角度与侯仁之先生类似。王宋文《畅春园兴废于何时》"对畅春园兴起的缘起和时间、基本建成的时间、兴盛和衰落以及近代以来的变迁作了探讨。其文以康熙帝亲制的《畅春园记》为根据,认为畅春园兴建的原因主要是康熙帝在处理政事之余,为了便于休憩而建。此外,其他一些著作和文章也对畅春园有所涉及,如《三山五园旧影》《二泉映月五园生辉——北京西郊的水系和园林》《畅春园——碧玉青黛》《北京西郊畅春园记略》《松轩茅殿萦带芳流——畅春园》等,但这些文章和著作多以介绍性为主,较少进行深人探索。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畅春园得以兴建的条件及其建成后所发挥的功能作一叙述,并对畅春园的功能与其兴衰之间的关系作一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畅春园得以兴建之原因
一处园林,尤其是一处皇家园林,所得以建成的最重要的条件莫过于优越的自然地理因素。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海淀附近的地形可以概括为两大部分,海淀台地与巴沟低地。海淀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平均海拔50米,而海淀台地海拔则在50米以上,最高之处在海淀以南台地的西半,平均可达52米以上。巴沟低地在海淀西南约2公里处,海拔49米,向北地形逐渐下降,平均海拔降至47.5米。其西以昆明湖与长河东堤为界,其东则以陡峻的斜坡与海淀台地形成显明的对照。畅春园就选址在这片低地上。这里地势低下,是河流、水源较易汇集之地。蒋一葵《长安客话》记载:“水所聚曰淀。高梁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滮灑四出,淙汨草木之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远树参差,高下攒簇,间以水田,町塍相接,盖神皋之佳丽,郊居之选胜也。北淀之水来自巴沟,或云巴沟即南淀也。”足见此处水源之盛以及自然风光之优美。尤其是水上风光更是为此增色不少,也为园林在此处的兴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畅春园便是汇聚了海淀台地西侧巴沟低地上丰沛的水源而得以兴建。正如著名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所言:“北京的西郊,西山蜿蜒若屏,清泉汇为湖沼,最宜建园。”
海淀此处良好的地形与水源条件早在明代即已为时人所重视。在畅春园建成之前,这里已有过清华园、勺园等有名的园林。而明代后期戚畹武清侯李伟的别墅清华园正是畅春园的前身。史载清华园“引西山之泉汇为巨浸,缭垣约十里,水居其半。叠石为山,岩洞幽眘。渠可运舟,跨以双桥。堤旁俱植花果,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京国第一名园也”。当时的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可见此处是以水取胜的一处优美风景。明末清初易代之际,清华园衰落,清初归肃亲王豪格所有。康熙初年,豪格的后代将其献于康熙帝。康熙年间又加以葺治,“视旧址十存六、七”,并利用了当时尚存的苍苍古树,建成后赐名“畅春园”,取《易经》“乾元统天,则四德归之,四时皆春”之意。只不过清华园是作为私家园林而存在,而畅春园此时已成为一座辉煌的皇家园林了。
除了自然环境优美之外,交通条件的便利也是畅春园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海淀地区位置适宜,距离京城亦不甚遥远,仅有十二里之距,便于皇帝的时常往来。当时多是由西直门或德胜门出发,经由南北向的道路抵达畅春园。根据尹钧科先生的研究,清代北京的陆路交通与前代相比有很大的发展,新增了几条皇家御道,其中之一即是出西直门经高梁桥、海淀到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等的道路。且由京城到西郊园林的御道皆以巨石铺砌,绝无坑洼颠簸、泥淖陷足之虞。不仅如此,这些御道还经常被予以维修。雍正二年谕旨,西直门外石路以及修至高梁桥、畅春园的石路有损坏者动用内库银两着加修理。不仅修复遭损坏的石路,雍正年间还曾在从西直门、德胜门至畅春园沿途皆种植柳树,“雍正二年奉旨自西直门、德胜门至畅春园沿途皆着种柳,岔道亦着栽种”,“四年奏准西直门至畅春园栽柳九千二百九十七株,德胜门至娘娘庙栽柳三千二百三十四株……”这种道路维修工作以及对道路沿途的美化,无疑为清代帝王出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畅春园建成之前,清帝主要的驻跸之地是玉泉山。顺治十三年(年)时,玉泉山静明园行宫建成。顺治帝在位时,曾经驻跸于玉泉山;至康熙帝时,虽于康熙十六年(年)时建成了香山行宫,但在畅春园兴建之前,康熙帝还是以驻跸玉泉山为主,多次于玉泉山处听政。当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帝驾临玉泉山的次数便明显减少;相反,驻跸畅春园的记载则屡屡见诸史书,“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分之二”"。之所以有如此变化,距离上的便利以及道路条件的改善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香山、玉泉山与畅春园相比,距离京城则明显偏远得多。驻跸于畅春园,于皇帝而言,在欣赏美景、游玩休憩的同时,可以兼理朝政,可谓一举两得;对大臣们来说,畅春园建起之后,其周围又有许多小园林随之兴起,其中多有王公大臣的赐园(只是这些小园林归内务府管辖,并不世袭)。这样一来也可以免去朝臣们为上朝谒见而长途奔波的沉重负担。同时这里又摆脱了城市的喧嚣和嘈杂,相比于京城,自是一处幽静之地。
兴建皇家园林同时也是皇帝个人兴致的体现。“夫帝王临朝视政之暇,必有游观旷览之地”,畅春园即是康熙帝的游憩之地。其亲制的《畅春园记》就记录了他兴建畅春园的内心动因:“朕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当时韦曲之壮丽,历历可考,圮废之余,遗址周环十里。虽岁远零落,故迹堪寻。瞰飞楼之郁律,循水槛之逶迤。古树苍藤,往往而在。爰诏内司,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计庸畀值,不役一夫。宫馆苑繫,足为宁神怡性之所”。一代帝王,常年日理万机,自然也需要与常人一样有所休憩和放松,畅春园便为其提供了这样一处地方。此外,康熙帝还是一位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着广泛兴趣的帝王,故而园中还建有司天台、数学等研究之所。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帝除经常驻跸于此处理政事外,还曾多次传召法国传教士张诚至园内清溪书屋讲授几何学等。五园中的其他几处,如雍正帝兴建的圆明园、乾隆帝兴建的清漪园等,可以说也是这种皇帝个人兴致的一脉相承。
自然,畅春园之得以兴建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清初人主中原之时,“于马上得天下,习为朴简,以骑射为事,园林之乐,非所素耽。而兵事倥偬,更无暇于游豫”"。康熙时平定三藩之乱,政局较为稳定,加之此时历经多年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状况已有所改善,因此具备了兴建园林的基础。即便如此,畅春园的修建也仍是“就明戚废墅,节缩其址”。另外,康熙帝在二十三年(年)至四十六年(年)中曾经六次南巡,而畅春园建成于二十六年(年),加之园内诸景与江南园林又多有相似之处,又聘请江南园林名匠张然进行建造,同时《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或便道,或于塔湾纡道临幸,此圣祖南巡例也”。可见康熙帝南巡时确有途经江南的众多园林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畅春园的兴建亦包含着康熙帝对江南园林的歆羡之情。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畅春园最终得以建成。康熙二十六年(年)康熙帝首次驻跸畅春园。其后更是经常驻跸于此,园居听政或处理各种事项。而畅春园由此也开始进人清代“三山五园”的历史,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畅春园之功用
畅春园在有清一代尤其是清前期发挥着多种作用,包括在政治上和帝王的日常生活休闲中,而这些作用的发挥也表明畅春园并非单一的纯欣赏性的园林。
从布局来看,畅春园内分东中西三路,园内景点众多。据《清通志》记载,“宫门内中为九经三事殿,后为春晖堂,其后为寝殿,曰寿萱春永。其后为云涯馆,馆后踰桥循山而北有河池,南北立坊二,为玉润、金流。门内为瑞景轩,轩后为林香山翠,又后为延爽楼,楼左为式古斋,斋后为绮榭园,内筑东西二堤,各数百步,东曰丁香堤,西曰兰芝堤,皆通瑞景轩。西堤外别作一堤曰桃花堤。东西两堤之外河流数道,环绕苑内,出西北门,闸注于垣外。云涯馆东南角门外转北为剑山,南为澹宁居。前殿为康熙年间圣祖御门听政引见之所,后殿为皇上旧时读书处。由大东门土山北循河岸西行为渊鉴斋,后临河为云容水态。左廊后为佩文斋,斋后西为葆光斋,东为兰藻斋。渊鉴斋之前为藏辉阁,佩文斋之东为养愚堂,相对为藏拙斋。小东门东垣内溪北为清溪书屋,后为隳和堂,西为藻思楼,后为竹轩。春晖堂之西出如意门为玩芳斋,山后为韶松轩。二层宫门外船坞之西为无逸斋。皇上诣园问圣母皇太后安每传膳视事于此。凝春堂在渊鉴斋之西,其东室为纯约堂,其右为迎旭堂。纯约堂东为迎凉精舍,迎旭堂后为晓烟榭。河岸以西为松柏室,其左为乐善堂,河上有阁曰蕊珠院,其北为观澜榭,蕊珠院西踰桥而北为集凤轩,轩后度河桥而西为俯镜清流,又循河而南即苑之大西门,延楼列亘,其外即西花园之马厂也。畅春园西南垣为西花园,正宇为讨源书屋。皇上问安之便率诣是园听政,中有阅武楼,为肄武之所”。此外还有恩佑寺、恩慕寺等。其中,东路南起云涯馆东南角门外,北至恩佑寺。中路南起大宫门,北达延塽楼。西路南起玩芳斋,北至小西门以北。园内重要建筑的职能各有所专。中路的九经三事殿是畅春园的正殿,九经是指儒家的九部经籍,即《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三事则是指汉代设置的辅政三大臣:司徒、司空、司寇。以“九经三事”作为殿名,表明这里是循经守礼、处理国政的地方。澹宁居是东路的主要建筑,有前后殿各三间,前殿是康熙帝的议事殿堂,是康熙帝处理政务的地方;后殿则是乾隆帝幼时的读书之处。清溪书屋是康熙帝的寝宫,亦是传闻中的雍正夺宫的发生之地。西路的无逸斋在康熙年间则曾作为皇子、皇孙的读书处,到乾隆时,乾隆帝至畅春园向皇太后请安时,则常于此传膳办事。雍正帝即位后,在畅春园东北隅修建恩佑寺,为圣祖仁皇帝推福并供奉其御容。恩慕寺则建于乾隆年间,是乾隆四十二年(年)乾隆帝为圣母皇太后广资慈福而建。恩佑寺、恩慕寺这两座山门至今仍存。此外,在二宫门外还有买卖街,略仿市集贸易景物,供帝王游乐时消遣。
从整体上来说,畅春园也是集多种功用于一身的一座园林。其最主要的功能便是避喧听政。避喧听政是康熙帝修建畅春园的直接目的,也是建成之后畅春园发挥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这里也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处政治中心。在畅春园兴建之前,康熙帝经常驻跸西郊的玉泉山,并常常在那里听政。康熙二十六年(年)康熙帝首次驻跸畅春园,其后更是频繁往来于此。相比之下,驻跸玉泉山的次数则明显减少。康熙帝虽将畅春园视为宁神怡性之所,但也并不是仅仅将此处视为游玩之地而已,相反,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帝常常于此园居听政。据相关统计,康熙帝一生中年均园居理政时间达余天。驻跸畅春园时,康熙帝常常命各部院衙门章奏交送内阁,由内阁转送至畅春园听理。康熙帝更是常常从畅春园启行前往各地,例如南巡,巡视霸州、永定河、塞外以及拜谒孝陵等。康熙帝也常常在畅春园接见外国使者。康熙四十四年(年)罗马教廷特使多罗人京觐见,康熙帝曾在畅春园接见多罗,其后还请多罗游畅春园。五十九年(年)又多次于园内清溪书屋接见罗马特使嘉禄,并赐宴。同年,还于九经三事殿召见葡萄牙使臣。除此之外,畅春园的守卫森严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康熙三十二年(年)四月,将违法擅人畅春园东门的鸣赞塔林家人洪德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康熙五十六年(年)六月,因民人马林擅人畅春园九经三事殿事而对马林本人及相关步兵和值更之人都处以刑罚。
除于此处理政事外,畅春园也为清代帝王避暑、休憩调养及奉亲提供了场所。满洲人兴起于东北龙兴之地,相较于其他地区,那里的气候较为寒冷,满洲人的生活习性也因而偏向于寒冷。对于中原的气候,尤其是夏季的炎热可能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东华录》就曾记载了多尔衮意欲建城避暑的事情:(顺治七年)“秋七月乙卯,摄政王谕,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碱,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建造大城,恐靡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只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但当时并未能建成这样一处避暑之地。康熙帝时,夏季“溽暑难堪”的现象必然还是存在的,他本人就曾因天气炎热而移驻瀛台。因此,畅春园建成之后便承担了一部分避暑的功能。以康熙帝而言,每年的春夏季节尤其是夏季,除了巡视塞外之外,在畅春园中驻跸的时间也占了较大部分;雍正的《御制圆明园记》中说:“……圣祖仁皇帝……爰就明戚废墅,节缩其址,筑畅春园。熙春盛暑,时临幸焉。”选择在熙春尤其是盛暑之际到畅春园中,避暑的目的显而易见。而北京西郊的优越的自然山水条件正为夏季避暑提供了可能。而且不仅皇帝本人常常于盛夏之际前往畅春园,有时还于此时奉皇太后幸畅春园。畅春园优美宜人的景色使其成为一处避暑胜地,康熙帝曾作有《御制避暑畅春园雨后新月诗》,“园亭气爽雨初晴,新月胧胧透树明。漏下微眠思治道,未知清夜意何生”。兴建畅春园的本意之一是于此游憩,借以宁神怡性,因此畅春园必然要发挥其在这方面应有的作用。前已述及,畅春园之得以兴建的因素之一是利用了海淀地区有利的地形和丰沛的水源条件。西郊水泉清洁,于颐养有很大的便益之处。康熙帝便时常来此休息静养:“........夏季天热,懒于行走,朕于畅春园养身七十日,暑天不觉已过。朕体大好……”“……自疟疾痊愈之次日起,即可行走,自第七日起即骑马来畅春园……”可见畅春园为康熙帝日理万机之余提供了一个清静调养的处所。康熙五十七年(年)三月,群臣还曾奏请康熙帝暂驻跸畅春园,因其水之善,便于调养身体。对于康熙帝本人来说畅春园是一处可以使“烦疴乍除”的所在,同时康熙帝也将其当作重要的奉亲之地。康熙帝是一位非常注重孝道的皇帝,畅春园刚建成不久,他就曾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出西直门,驻跸畅春园;此后皇太后驻跸澹泊为德等行宫时,康熙帝还经常至此问安或请皇太后赏花。康熙五十六年(年)三月,康熙帝诣镜峰问皇太后安,并恭请皇太后于雅玩斋进膳、看梅花,还为此赋诗一首:“敬上乔松祝,欣瞻王母仪。捧觞称寿句,进酒问安词。……承欢同永日,孝思莫违时。会庆思经义,千秋古训垂十七年(年)春,畅春园群花开放时,还曾因清明祭祀皇太后而不肯前往。到乾隆帝时,更是将畅春园专门视作皇太后的高年颐养之地。帝王以及皇室的屡次亲临充分证明了畅春园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更说明了畅春园在宁神怡性以及调养身心方面的巨大价值。故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畅春园也是清代帝王提倡并践行孝养的一个体现。
畅春园虽是一处皇家园林,却并不是只有所谓的花花草草而已。在畅春园中还种有稻田,这些稻田的设置也可以说是康熙帝重农思想的体现,“临陌以悯胼胝,开轩而察沟浍”,并且“时往以省耕观稼,炎暑蒸郁,亦将以憩息于此也”。畅春园的西墙内,约有上百亩田地,种植了水稻和各种蔬菜,可以说是康熙帝的“试验田”。农业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基础,也是帝王所必须要关心的大事。康熙帝对农业和农事可以说是相当关切的,从他所作的诗作中便可看出,例如这首《早御稻》,“紫芒半顷绿阴阴,最爱先时御稻深。若使炎方多广布,可能两次见秧针。”?再如康熙三十九年(年)七月所作的《御制畅春园观稻时七月十一日也》,“七月紫芒五里香,近园遗种祝祯祥。炎方塞北皆称瑞,稼穑天工岁乐壤”;康熙四十二年,《麦秋盈野志喜有序》:“岁次癸未,夏至有事于方泽斋戒,自畅春园进宫,见麦气盈秋,田园茂胜,雨旸得时,稼穑有望。从来北方雨泽艳阳清和之际,每每难得,皆因去冬阴雪连绵,自春至夏未欠甘霖,所以草木花果罔不丰荣,人心谷价罔不和平,故志喜而为咏:……万亩皆齐诞降谷,千家秀实已登阡。先忧旸雨惟民疾,后乐时丰纪玉笺。……”除了关心稻田的情况之外,康熙帝对关于京城以及畅春园附近的雨水状况的奏报也是较为白殿疯去哪家医院好白癜风如何确诊治疗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hechizx.com/hcsmj/18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