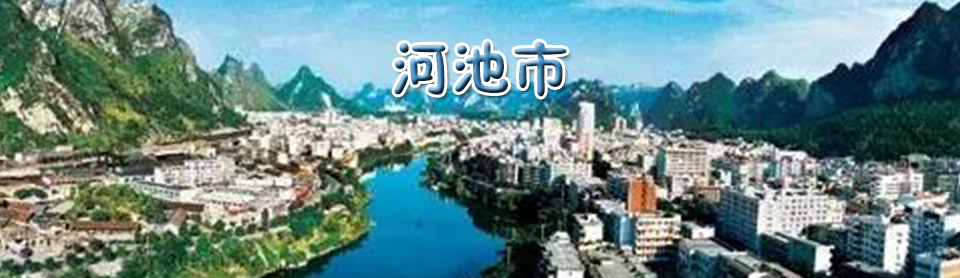河池作家覃克参散文父亲的故事
覃克参,壮族,困难时期生于桂西北边远山区农村(环江县驯乐乡)。在河池师专学了三年国文后年7月返乡谋食于杏坛;十年后从政,曾在县教育局、乡镇、县委县政府多个岗位任职;二十年后重返杏园操旧业,现供职于河池市委党校。上世纪90年代杏坛耕耘时偶尔涂鸦,散文、小小说、报告文学习作散见于《河池日报》《广西法制报》《广西日报》《广西教育》《中国民族教育》《三月三》等报刊。
父亲的故事·戒烟
文/覃克参
父亲的烟名闻名遐迩,是方圆几十里名符其实的“烟王”。
父亲烟龄很长。父亲年幼即孤,小小年纪就被迫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沉重的生活重压使父亲小小年纪就跟大人学会了烧烟。那年父亲还不满十岁,父亲的烟龄至少可以从十岁算起。
父亲烟量很大。只要不是吃饭睡觉,父亲几乎烟不离手。父亲吸烟不用烟斗,而是用草稿纸或烟叶包成喇叭筒。父亲的“喇叭筒”是特大号的,每只差不多要装上半两烟丝,能烧上十分钟。每天早上起床,父亲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卷“喇叭筒”并在焚烧首个“喇叭筒”过程中完成如厕、生火、喂猪等活计。接着父亲取回晾在廊檐下的生烟叶,一张一张地在木地板上铺平压实,然后紧紧地卷成筒,用尖利的斧头横切,细细的生烟丝就出来了。烟丝细黄细黄的,好像金丝。父亲有一个装烟的专用口袋,每天早上都要袋满这个口袋的烟丝方才出门干活。早上满载而出,晚上空囊而归。这些战绩归功于父亲不管是走路还是干活,只要嘴巴有空,必然呑云吐雾。
父亲烟瘾很深。烟不离嘴是父亲的特点,无烟罢工是父亲最大的特点。那年父亲去山上薅小米,爬到半山腰的小米地后,父亲还能舒服地品一只“喇叭筒”。可是等到第二只“喇叭筒”卷好后,那只不争气的打火机怎么也打不起火。父亲掏出专用烟袋内的火柴盒。真是祸不单行,火柴盒里也没有火柴子了!父亲无奈地摇摇头,薅地去了。劳作了一会儿,父亲又本能地掏出烟袋,再次使劲地摆弄打火机,任父亲怎么努力,均徒劳无功。父亲气愤地把打火机狠狠地砸到旁边的乱石堆上,收摊回家。尽管剩下的活路已不多,只要再干两袋烟功夫,便可大功告成,但父亲宁可明天再花一个钟头爬上山,也不愿现在遭受无烟的煎熬。还有一次,父亲外出搞副业,晚上在工棚里又断了烟火。父亲和伙计们为了取火点烟,竟然想出了将电炒祸烧红的馊主意。结果是锅没烧红电源线却先烧焦起火了。手忙脚乱地拔掉电源遏制灾情后,父亲笑呵呵地拿着“喇叭筒”就着火源津津有味地吞云吐雾。父亲说,他宁可没饭吃,也不能没烟烧。
父亲吸烟技艺很高。父亲自幼吸烟,日积月累练就了高超的吸烟技艺。父亲是个木匠,他可以在锯木头凿榫眼刨木板时不用停下手中的活路,仅用嘴巴就可以消灭一个个“喇叭筒”。不可思议的是“喇叭筒”的吸口竟不被弄湿。父亲可以猛吸一口烟,然后运气作法,烟从耳朵里冒出。也可以把烟吞进肚里,不再吐出。从父亲口中吐出的烟卷环环相扣可以拉出好长好长。
父亲很会种烟。父亲吸的烟是自己上山开荒种植的生烟。每年四月下种,十月收割。父亲种的烟,叶子大而肥厚,象蒲扇。烟收割回来后父亲用竹竿把它们夹成一排排,晒干后晾在廊檐下。每年有五六十竿,整整齐齐排在一起,远远望去熠熠生辉,很是壮观。这种烟叶除日光自然晒干外未经任何处理,是地地道道的原生态产品,味道比卡斯特罗烧的哈瓦那雪茄还纯正。父亲种的烟除供自己享用外,还略有盈余。每年母亲都可以拿点到集市上偷偷地卖(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个人卖东西是走资派),换点油盐钱。
父亲日夜与“喇叭筒”为伍,家人早已习以为常。尽管有时候父亲吸的那个生烟熏得家人睁不开眼,尽管有时候那个烟味呛得全家人呼吸不畅,但全家没有哪个人敢对父亲嗜烟说不。看到父亲有时烧烟时咳个不停,家人意识到应该提醒父亲少吸点烟了。可是父亲在家里的至尊地位使家人的意识只能是潜意识。直到有一年冬天父亲日夜咳个不停,甚至咳得彻夜未眠,我们才下决心让父亲少吸点烟,并劝父亲去看医生。
但是,父亲并不认为咳嗽与烧烟有关,也不认为咳嗽是病。父亲说咳嗽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从小就咳,是很正常的现象。每次劝父亲去就医,父亲都这么说。久而久之,似乎父亲咳嗽是正常的,不咳嗽就不正常了。
对于吸烟导致肺病引起咳嗽,父亲更是嗤之以鼻。父亲说,烟熏会致病?这简直是笑话!你们不见灶台上烟熏的腊肉,放个半年十个月,一点事都没有,就是隔年,也还是鲜香如故。如果离开烟熏,不说半年,就是留它个十天半月,都会生蛆。吸烟,好处多着哩!
尽管我们知道父亲说的是歪理,但是谁都不敢对父亲说不。因为那时候父亲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而我们都还是这个家庭的寄生虫。再说两个劳动力干活年年超支的家庭,能勉强维持生计已经很了不起了,实在难有余钱治病。
如此这般,谁都不能撼动吸烟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也很难说服父亲去看医生。
渐渐地我们几兄弟长大了,有的考上中专,有的考上大学。学成毕业后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吃上了皇粮。有了干部身份和固定收入的我们在家里渐渐地有了话语权。日渐丰厚的腰包也渐渐地为我们积蓄了底气。而父亲因为年纪的原因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武和至尊地位。此消彼长,父亲在我们壮着胆子用恩威兼具的语气劝他去看医生时,低下了他那一向高高昂着的头,他的咳嗽不是病的理论也被颠覆了。
医院检查身体,听诊、抽血、化验、拍片。折腾了一个上午,医生给出的结论是父亲患了慢性支气管炎。医生说,父亲这患的是慢性病,可能是长期大量吸烟引发的,一时半会儿难彻底治愈,得慢慢来。所以,不用住院,拿了药回去慢慢调理。于是开了大大小小的十数种药,让我们带回去给父亲服用,并叮嘱父亲少吸烟,最好是戒烟。还要求我们帮助父亲彻底戒掉烟。
父亲自幼吸烟,少年即吸食上瘾,青壮年时简直是嗜烟成癖,到老年时烟几乎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如此爱烟的父亲,要让他戒烟,简直比登天还难!
可是难归难,要治好父亲的咳嗽病,必须要让父亲戒烟!
回家后,我们即帮父亲拟制了戒烟计划,要求父亲一个月内彻底戒烟。谁知道戒烟计划刚一抛出,就触动了父亲倔强的神经。父亲当作我们的面把我们买的戒烟糖丢进牛栏里后,态度坚决地说:“药可以吃,烟不能少,更不能戒。要是一定要戒烟,这药我也不吃了,让它去喂牛!”
看着父亲稀疏而花白头发下那张倔强而坚毅的脸,我们妥协了。我们同意父亲先用药,戒烟的事以后再说。
可这“以后再说”最终演变成了以后不能说。也许是父亲从这次的戒烟斗争中看到了我们的弱点,自那以后,我们每次提出戒烟的事父亲总是倚老卖老不予理睬,我们逼紧了,父亲干脆表演寻死觅活的把戏,宁死不从。
最终我们败下阵来,谁也不敢再提此事。“喇叭简”仍然是父亲的密友。只是细心的人发现,父亲的“喇叭筒”精瘦了许多,上手的密度也小了许多。父亲一边服药调理,一边照旧地吞云吐雾。咳嗽虽然没有明显好转,倒也没有加剧的迹象,久而久之,又成了习惯,我们也就又听之任之。
时光飞逝,父亲很快就要进入古稀之年了。就在我们谋划着帮父亲办七十寿辰活动时,父亲病倒了。父亲说胸口剧痛。住院观察检查后医生说是父亲的肺出现了问题。当父亲在病床上准备卷“喇叭筒”时,被医生制止了。医生严正地告诉父亲他的病就是因为吸烟引起的,今后再也不许吸烟了。说完还把父亲的烟袋没收了。胸口剧痛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医生把他命根子般的烟袋拿走。
两天后,熟识的主管医师悄悄告诉我们情况可能不妙,医院看看。
医院进行全面复查后,CT室主任指着父亲CT片上肺部的一处阴影说:“靠近大动脉处有个可恶的东西,晚期了,不大好办。”主管医生向我们推荐了两个治疗方案:一是搏一搏,动手术割掉。这个治疗方案如果成功,效果较好,但因为太靠近大动脉,病人又上了年纪,风险很大。搞不好会下不了手术台。二是不动它,保守治疗。这个治疗方案风险小,但效果不会很好。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最终选择了第二个治疗方案。
方案选定后,医生为我们制定了短长结合的具体方案。短期内住院治疗,用药物消除疼痛,恢复体力。等到体力恢复到一定程度后回家用药,辅以食物疗法。在父亲住院期间,我们几兄弟每天24小时轮流在病榻前小心服侍。
没过多久,父亲说他已经能自理了,不要我们再来陪他了。再过几天父亲坚称他的病已痊愈,坚决要求出院。
父亲要求出院的态度过于坚决而强烈,使我们不得不猜想父亲出院的动机不纯。大家揣测肯定是父亲想念他的“喇叭筒”了。
经不起父亲的再三闹腾,医院终于同意父亲出院了。
父亲出院时虽然不是生龙活虎,却也步伐稳健。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预感到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不能对他太苛刻。生烟味道太浓烈、太呛,父亲回家前我们把他的那些生烟叶全部卖掉并为他准备了质量较好味道较淡的烟卷。我们做好了父亲见不到廊檐下他那一排排生烟时暴跳如雷的思想准备。意外的是父亲看不到他的生烟竟然没什么反应,心情静如止水,甚至连烟的去向也不问一声!我们猜想这可能是暴发前的沉默。我们不能让他暴发,于是立即给父亲递上一条玉溪烟卷。没想到父亲竟摆手拒绝说:“我不吸烟了!”说这话时父亲目光坚毅,神情庄重。
“烟王”不吸烟了,这在我们村是爆炸性新闻。但村人认为这是日出西隅,流水上山。赌场常胜将军云三公拿出自己栏下唯一的母猪与村人下注:不出半月,“烟王”还是吞云吐雾的主儿。二十天后,云三公的母猪成了村人的下酒菜。村人再也没有人怀疑父亲戒烟的真实性!
毕竟父亲得的是绝症,虽然彻底地戒了烟,但病入膏肓时不是外力能改变结局的。父亲还没等到他的七十寿辰就走了。弥留之际,父亲要我给他卷只“喇叭筒”。我疑惑:“您不是戒烟了吗?”父亲说:“对,我是戒了,但我从来没有忘记它。我戒烟是因为医生告诉我吸烟使我生病。而我生病后,你们花费钱财不说,你们为照顾我而忙碌和憔悴比病魔对我的折磨还厉害。”
父亲戒烟的理由是如此的简单而深沉!
老鸟传媒——
致力于全市文学艺术、文化及教育的解读和推广
致力于公益广告、微电影、专题片的制作及发布
致力于城市文化创意设计,让城市更有人文情怀
广告联系
老鸟传媒:打造城市终端情怀
转载请注明:http://www.hechizx.com/hcsmj/19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