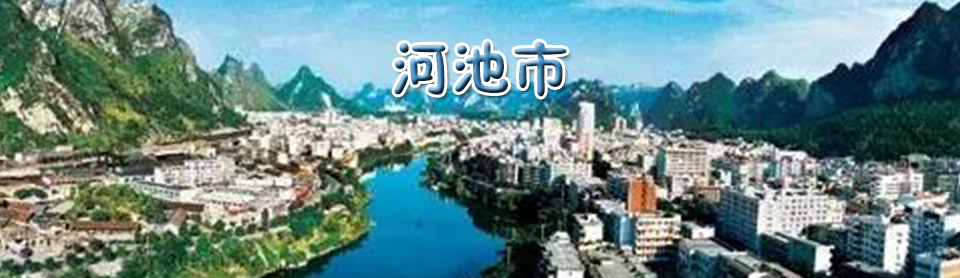重磅推荐红日bull乡土叙事
和万人一起品读河池看世界!
精彩前奏多重阐释的空间?张柱林
红日的小说《码头》,读来饶有兴味,貌似简单,其实又非常丰富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红日之前的小说,一般以主题或题材作为命题的主要考量因素,而《码头》却是以地点或空间作为着眼点。初看之下,似乎“码头”作为题名,并不特别切合小说的整个主题和所描述的对象,作品主要写的人物是老麻,他管理的是渡船,而不是码头,以码头为名好像偏了。仔细一琢磨,又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用心。没错,老麻是船夫,他的工作是开船把客人送到对岸去。码头是他的船停泊的地方,也是他等待客人或客人等待他和渡船的地方。一般的理解,码头是集散人货的场所,也是沟通和交流的场所,本身应该是开放的。吊诡的是,至少在汉语里,码头的引申义常常用来指一种封闭的场域,管理者据公为私,形成帮派、圈子,排斥外人和外来事物,这正是今天官方所反对的“码头文化”。老麻家世袭和垄断了当地的渡船业务,确乎将渡船当成了自己的“码头”,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矩。其中的一条规矩就是要过河的客人不能喊老麻“开船”,因为当地土话(属壮语方言一支)里,这句话里有谐音“麻子”的意思,老麻脸有麻子,忌讳别人提及所有与麻子有关的东西。当地人都知道这个规矩,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言语上冒犯老麻,所以这不会成为问题。
小说正是从有人坏了规矩开始的。这天来了一个陌生人,偏偏连喊几声“开船”,导致不痛快的老麻停渡三日,积压了大批要渡河的客人。老麻这样做,当然是表现自己权力的任性。本来这也不会成为问题,老麻气一消,自然就开船了。问题在于这位不懂老麻规矩的陌生人,竟然是新来的乡长“眼镜”。这是小说给我们制造的第一个意外,也是新乡长给老麻制造的第一个意外,后面就是一连串意外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老麻自己反而成了不懂规矩的人,而且后果很严重。显然,在老麻的码头之外,还有更大的码头笼罩着世界。小说为我们揭示了由此引起的巨大不安:老麻立即戒掉了自己多年喜欢吃的“猪红”,改吃小米粥;他每天提前到码头观察,看看客人中是否有戴眼镜的新乡长,他想与之“和解”;他怀疑新乡长为了惩罚他,决定在河上建一座桥,显然桥一建成,两岸人民将立刻用脚投票,过河采用过桥的方式,而不再使用渡船的方式,想一想,谁愿再受老麻的气,他那些不成文的旧规矩,人们忍了多少年了,无非是受了过河只有老麻的渡船这个唯一选择的要挟。如果小说只写了这些,其实也相当有意思,其讽刺的内涵也展示得淋漓尽致了。
必须承认,《码头》可以有另外的读法,而且可能并不比上面的解读不合理。比如,桥与船的冲突。原先,两者的功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连接两岸,便利交通,同时,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存在理由,至少是互补的。老麻能够掌握自己的“码头”,并且在听到政府即将在河上建桥的风声后,仍然泰然自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就两岸的人口和经济状况来看,建桥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成本太高而收益太低。但现实就是那么任性,河上的铁索桥就是建起来了。桥是老麻渡船的竞争对手,而且是一个过于强大的对手,他面临灭顶之灾,过河的人如果再也不坐他的船,他的生计危机就降临了。他的所有技能(如会游泳)和资源都是为渡船准备的,他只能靠船和水维生。更重要的是,新桥的建桥地址正好是在原来的码头和航线上,这简直是釜底抽薪,他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试图找到新的出路,如开船到河中电鱼来卖,但这是违法的。他也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如新桥由于洪水带来的大树撞断了一根铁索发生倾斜,导致当时正过桥的8个人掉入河中,老麻不计前嫌,积极开船救人,并将遇难者打捞上岸。他并非坏人,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但他的想法确实有一定道理:那几个遇难者如果不从铁索桥上过河,而是乘他的的渡船,不就逃过一劫了嘛。但铁索桥的好处一目了然,所以老麻还是被无情地抛弃了。那幅景象,似乎正应了古诗所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其实老麻也并非完全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人,他也曾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船装上柴油机,改装成了负载能力更强的机动船。但这显然无济于事。时势弄人,老麻作为历史洪流中的个体,自然无力抗拒。虽然他表示自己宁死也不上桥,可这改变不了人们舍船就桥的局势。
我们还可以将小说读成一个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不充分所导致的悲喜剧。从新乡长一面看,他不了解老麻的规矩或禁忌,导致自己无法渡河,必须绕道走大弯路,枉费了许多气力。当然,由于他掌握的资源远比老麻这个小人物多,所以老麻的自大丝毫无损于乡长的权威与力量。就像老麻所想像的,乡长可以下令修桥,一劳永逸地解除老麻利用停渡摆谱的威胁;他可以指示司法人员执行法令禁止电鱼,让老麻失去生财之道;他可以修路,让人们从其他地方过河,让老麻的船成为废船;他还可以雇佣其他人守桥,让大家认为本该获得此职位的老麻失业……当然这些可能都出自老麻的猜测,因为他认为自己得罪了乡长,乡长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报复自己。根据小说最后的揭秘,我们知道,其实围绕着修桥所发生的一切,根本与乡长无关。当读者获知这一消息时,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老麻已经死了二十三年。老麻由于没有掌握相关信息,终日处于巨大的惶恐中,在他身边发生的事情都被他错误地感知和理解。话说回来,在这种类似闹剧的误解中,却又折射出巨大沉重的真实,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庸人自扰的故事。小说在其中又设置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情节:乡长其实上过老麻的船,他号为“眼镜”但并不戴眼镜。而老麻一直耿耿于怀的的,就是乡长始终没有上过他的船,让他寝食难安。这又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恶果,“眼镜”不戴眼镜,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这是老麻儿子怕父亲死不瞑目,在其临终前安慰他的话,很可能是谎言。
当然,我们的阅读可以把重心放在老麻这个人物身上。老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自认为老大,又想当然地把周围发生的一切都视为和自己有关,是一个自大又自怜的人,同时,在他认为自己开罪乡长后,其所作所为却是可笑、可悲又可怜,他的悲剧有自身性格缺陷的因素起作用,比如同在修桥时由于码头上的店铺被拆而失业的老潘,就因为信息灵通或转寰得快,获得了守桥的职位,而老麻却意外地丢掉了这个本应该属于他的工作。同时又必须看到,他的命运其实又为他无法左右和控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小说最后揭示谜底,修桥一事是上级布置的扶贫攻坚项目,无论是乡长或老麻,他们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事实,用我们曾经熟悉的话说,就是事物的发展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扶贫是一项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的巨大历史规划,将从根本上改变无数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一点,老麻并不知道,但小说家用自己的作品,通过他这个形象展现给了读者。
阅读精彩码头
◎红日
那天早晨,老麻在市亭里吃了一碗“猪红”。码头上的人不叫“猪红”,叫“血旺”。吃到第三口时,老麻咳了一声。旁边有人对他说:你流鼻血了。老麻用手抹了鼻子,掌面上果然有鲜红的血丝。当然是猪血,猪血随着老麻的一声咳嗽从食管里倒灌出来了。走向码头,老麻安慰自己,这是一声很自然的咳嗽,几滴很正常的猪血,并非什么凶兆。来到船上,老麻继续安慰自己,不想心头却燃起一股火苗,火苗源自对岸的一声喊叫。当时老麻刚刚做通自己的思想工作,稳定了情绪,对岸有人用本地话喊了一声:开船!这个充满磁性的男声,音域宽阔音调高亢,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不但老麻听见了,估计河两岸的人也都听见了,老麻心头的火苗连同嘴上的烟头重新燃起。老麻划了一辈子的船,从未有人喊他“开船”,并且这样大声地喊叫。对岸的人以为老麻耳背,再喊一声:开船!开你个卵!老麻骂了一句,他吐掉嘴上的烟屁股,“哗啦”一声将铁链拴到铁桩上,望也不望对岸一眼就扬长而去。
破天荒喊了这声“开船”的是“眼镜”。“眼镜”是乡府新来的乡长,那天他履新大吉,从县城来报到。当时“眼镜”伟人似的双手叉腰,放眼宽阔的红水河面,满脸春风,底气很足地朝对岸停泊的木船,响亮地喊了这么一声,既是发号施令,也是正常提示。过渡嘛,自然要开船。“眼镜”不知道这一声“开船”犯了禁忌,或者坏了码头的规矩。在这个码头过渡的人是绝对不能喊“开船”的,本地话“开船”反过来讲,是叫他“麻子”,这就骂老麻他老人家了。你只能默默地等船,然后上船。上了船也不能催促他开快一些,方言“开快一些”反过来讲,也是揭他老人家的短。乡府干部也一样,也要管好自己的嘴。乡府干部上了老麻的船,就和吊在水里的桨橹一样攥在他的手里了。这不能怪老麻,要怪就怪这个码头的说话方式。这个码头的人喜欢讲反话,就是将方言倒过来讲。当然,你讲官话是另一码事,问题是你讲官话老麻他听不懂,最好是默不做声。也有人招呼老麻一两声的,招呼的词语是“过渡”。对,过渡。一声“过渡”多么贴切,多么自然啊,它不仅巧妙地规避敏感的“开船”,还有讨好的成分在里面。喂,老麻,你看我们多么尊重您啊。“过渡”确实更胜“开船”一筹,别开敏感的因素不说,单从词义来理解就不一样,“开船”带有命令的口吻,“过渡”则是请示或者报告。前者居高临下,后者低三下四;前者刚性,后者柔软。这样的词语不用分析评估,一听就听得出来。那些叫“过渡”叫得特别温柔的声音,往往容易打动老麻。老麻通常要凑够一船渡客才划桨,这个时候纵然对岸没有一个渡客,一声温柔的“过渡”却能启动老麻手里的桨橹,悠然地将船划过来了。
初来乍到的“眼镜”,哪里知晓这个码头的禁忌或者规矩,他不仅大声地喊了两声“开船”,而且朝老麻上岸的背影持续不断地重复了三遍。过渡对“眼镜”来说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他重复讲了三遍。几声“开船”不但没有唤回老麻,反而加快了老麻上岸的步伐。老麻在心里忿忿地说:有本事你游过来。老麻的目的很明确,不能让此人坏了这个规矩,凡事一开头就不好收场,必须将它消除在萌芽状态。老麻上岸后找人下棋,研究他的楚河汉界去了,将“眼镜”滞留在河右岸。“眼镜”那天过不了河,并导致两岸的渡客都过不了河,酿成了码头有史以来的停渡事件。
老麻停渡一连停了三天,停了一个圩日的时间。直到三天后的下个圩日,老麻才回到船上。累积了三天的渡客,将码头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有些是当天的渡客,有些是三天前和“眼镜”一起被滞留的渡客。大伙都默不做声。沉默是当前最好的姿态,绝不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你爆发看看,除非你不想过渡了。他们大多都知道了停渡的原因,他们原以为这个禁忌只是说说而已,玩笑而已,没想到老麻是不开玩笑的,这个玩笑是万万开不得的,老麻果然是那样神圣不可冒犯。有人讨好地递给老麻一根带嘴的香烟,双手划桨的老麻不屑一顾地拒绝了。他心里哼了一声,一根带嘴的香烟就想抵消一声“开船”,没那么简单,对你们这种人不仅要观其行,更要听其言。停渡三天,让渡客们醒悟到,在这个码头上,必须知晓红线、守住底线、不踩高压线,一句话,就是要讲规矩,再通俗一点,就是绝对不能喊老麻“开船”。
渡了三批次渡客后,老麻泊了船上岸去找老潘。彼时正值圩市红火时段,人们忙着交易,暂时没有人过渡。老潘独自一人经营右岸一家供销分店,一个人守着六眼房子,里面摆一些盐巴、米酒、煤油、棉布、锅碗瓢盆之类生活用品,空荡荡的房子成为自行车的寄存处。渡客寄存自行车,上锁的老潘收取三毛钱;不上锁的分文不取,下班后老潘会选择其中一辆车子骑回家。有车主心疼爱车让老潘骑了,宁可辛苦也将车子扛到码头,却让老麻打发回去。老麻说,摆渡木船,不许人车混载,这是上面的规定,也是规矩。
老潘一见到老麻,指着他塌陷的鼻梁道:你这回是彻底地坏脸了。“坏脸”是方言,距离“坏身”只有一步之遥。老麻那张布满麻豆的脸本来就“坏”了,现在被老潘宣布“彻底地坏了”,等于宣布报废。方言“坏脸”含义比较复杂,一两句话很难翻译到位,引申过来相当于“问题十分严重”。老潘说:你知道过河的人是谁吗?是新来的乡长。老麻一怔,直到此时他才明白喊他“开船”的竟是乡长,不!是新乡长。老乡长跟他熟稔,从未喊过他“开船”。老麻上岸来找老潘,其实也就是打探那天喊他“开船”的是何方大侠,同时还要发泄一番,通过老潘这个平台表示他的谴责和抗议,敲山震虎,以正视听。老潘以酒代茶递给老麻一杯,老麻抿了一口,脸即变了颜色,由猪肝色变成核桃色,那是脑部供血不足的症状。他喃喃地说:只要人在岸上,总要上船的……老潘打断老麻:“眼镜”当天和他的随行绕道邻县,通过那里的一座大桥到达左岸,再沿着蔗区公路到了乡府。
老麻像断奶一样戒了“猪红”。吃奶已没有记忆,吃“猪红”是有记忆的。“猪红”是他的最爱,他每天把“猪红”当作早餐吃,百吃不厌。现在老麻的早餐变成了玉米粥。吃了玉米粥,老麻早早就来到码头,比以往足足提前了半个小时,以致到对岸接送邮件的老黄产生了错觉,以为他那块上海牌手表昨晚忘了上链。从这一天起,老麻格外留心观察每一位渡客,这从他斜眼睨视别人的细节可以看得出来。老麻从来不会正眼看一个人,哪怕瞪你一眼也不是正眼。偶尔正眼看一个人的时间不会超过两秒。他正眼看着的事物只有一样——河面的漩涡。事实上老麻对往返于这个码头的渡客了如指掌,哪些是熟客,哪些是生客,他一眼就瞅得出来。哪个是乡府、食品站、供销社的,哪个是粮所、营业所的,他甚至能叫出名字来。后来老麻将目标锁定为戴眼镜的。锁定这个目标也是毫无意义,老麻对两岸上戴眼镜的同样了如指掌。左岸是乡直机关所在地,戴眼镜的有乡府覃助理、中学陆教导和温老师、供销社洪主任。右岸吃皇粮只有老潘一个。老潘只有阅读邮电所老黄分给他的《参考消息》才会戴上眼镜。严格来说,戴老花眼镜的人不能归为“眼镜”之列。
一个月过去了,老麻没有发现一个陌生的“眼镜”渡客上他的船。连续有两个星期,乡府干部倾巢而出,频繁过渡,甚至有几个晚上也要渡河。老麻知道这是开展“计生突击宣传活动”。在此之前,老麻曾经有个预感或者危机:在不久的将来,码头就会出现另一艘渡船来。他甚至还窥见一个极为严肃的会场,会场里灯火通明,白炽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会议专题研究码头停渡事件,一乡之长被滞留,那还得了!岂能容他老麻这样霸道,想摆渡就摆渡,想停渡就停渡,岂能如此容他无法无天!最后乡府决定上报有关部门购买一艘汽艇,作为乡直机关干部过渡专用船。老麻在一阵突突突的电机轰鸣声中醒来,码头还是他的码头,渡船还是他的渡船。老麻家族“统治”这个码头已逾百年,到他这代“老大”已是第三代。这条百年老船传到老麻手上后,他给它装上了柴油机,不过仍然保留桨橹。枯水季节老麻还是划桨,柴油机只有汛期才会用上。然而这一个月来,老麻在船上除了见到覃助理外,没见到第二个“眼镜”。老麻纳闷了,难道这家伙上任后就不下村,就守着办公室手摇电话,发号施令。难道他偶尔下村或者到县里开会总是绕到那座远远的桥,从那里到达彼岸。老麻心里想,一个月你可以这样,一个季度你可以这样,可是一年、一个任期你都可以这样吗?不可以的,也不可能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在岸上,总要上我的船。
老潘亲自将消息送达到码头上。消息不是参考消息,而是切实可靠的消息。老潘说正好你泊船在这边,不然我要喊一声“开船”了。老麻说:你敢!老潘说门市部的门没锁我就下码头来了,他的语速很急,像汛期的河水。昨夜来了两辆十轮大卡车,分别在门市部前面的空地上卸下钢索和木板。早上,县供销联社来人,清点门市部的商品,清退屋内寄存的自行车,将门市部变成指挥部,乡府要在河上架起一座铁索桥……老麻听得心跳加速,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关于这河上的桥,已不再是天方夜谭。
关于桥,关于这河上的桥,老麻不是没听说过,而且桥的话题从来就没停止过。都是渡客们说的,似乎专门或者存心说给老麻听。渡客们说:这河面上要是有一座桥就好了。老麻心里说:那敢情好啊!但这可能吗?这河两岸多少人,架这么一座桥得多少钱,合算不合算?这不是你们想架就能架的,这是需要市场评估的。最后老麻给出一个结论,四个字:天方夜谭。老麻却不当面反驳,他默默地记录高谈阔论架桥的渡客,时不时给他们一个冷板凳。码头上自然一只板凳也没有,有的是冰凉的石头,你们就坐在石头上谈论架桥吧,凑不够一船人,我是不摆渡的。久而久之,渡客们意识到,这“架桥”和“开船”一样,在老麻面前是不可轻易出口的。老麻当初的结论肯定有他的道理,但道理也不是一成不变,到了一定的时期,道理就不是道理了,或者不是硬道理了。危机如同汛期终于来临,铁索桥一旦架起来,这码头就不存在了,渡口不存在了,岸也不存在了。老麻的船当然可以存在,但已不是渡船,是一只孤舟了。老麻一下子回到唐朝,和他的船成为柳宗元笔下的绝句,后面两句好像是这么说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渡船上的渡客肆无忌惮地谈论架桥,他们不再规避这个敏感的话题。不知好歹的居然胆大妄为地将它与“开船”勾连起来,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说案例。他们说:打死我们都想不到,一声“开船”竟然开出一座铁索桥来。尽管他们装模作样很别扭地用官话表述,但老麻一听就听懂了,不但入耳入脑入心,而且融会贯通了。老麻恨不得立马掉转船头,送他们回到原地继续感叹,无奈船到码头车到站,如同他触手可及的命运已经无法扭转或者拐弯。
汛期明显提前,往年是吃了粽子祭了屈原河水才动容。眼下卖糯米的商客还没过河,河水已开始变浑、变急、变得桀骜不驯。汛期前老麻需要对柴油机进行清洗,维修。这项工作需要两三天时间,最快也要两天。这两三天实际上也就是停渡,但此“停渡”非彼“停渡”,不属于事件。渡客们都清楚,这个时节单靠老麻手里的两把桨橹,是无法安全将他们送达对岸的。时间不是第一,安全才是第一。眼下急转直下的形势让老麻有些措手不及,形势包括提前的汛期,包括顺势而生的铁索桥以及为之奔忙的乡干部、设计员和工程师,他们频繁过渡,马不停蹄。按照老麻的性格或者心态,他应该是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确实,你们架桥关我吊事。然而夜里老麻还是将他的三个儿子招呼来了,三个儿子分别读乡中学和小学。船上,老三举着马灯,老大老二当他的助手。只一夜工夫,老麻就把柴油机维修好了。柴油机发出稳妥踏实的声音时,老麻点燃香烟连吸几口,摇了摇头,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老麻最清楚自己,他在惦记一个人。铁索桥都动工了,你还在岸上指手画脚。官僚主义要不得的,你还是乖乖上我的船吧。
铁索桥的桥址选择在码头附近,正好和渡船航向重叠。老麻现在的航向将是铁索桥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老麻家族用一条船在河面上开设的通道,将由一座腾空而起的铁索桥代替。照老麻理解,渡船航向通常选择在宽阔河段,这是因为宽阔的河面水流平缓,狭窄的河段波涛汹涌。架桥就不一样了,桥址要选择在狭窄的河段,以缩短里程,减少投资。这是用脚趾头都可以想明白的事情。可是已经施工的铁索桥竟然是从宽阔的河面上过的,是直接从老麻的头顶上过的。老麻怀疑,他们可能连选址都没选,直接就按照他的航向过了,简直就是他怎么划船,他们就怎么架桥。开始老麻分析一定是哪个工程师的脑子进水了,进一步推敲,事情绝没那么简单,完全是有所指向的,是有针对性的,带有典型意义的。一句话,“眼镜”是彻底地跟他杠上了。这杠不是一般的杠,是破釜沉舟,是要让他老麻彻底地从这个码头上消失。
老麻每天正常摆渡,原本就寡言少语的他,几乎变成了哑巴。渡客们异常活跃,船到河中就仰面朝吊在钢索轿厢里的施工员喊叫。那几根粗大的钢索什么时候从头顶上架设过来了,老麻连感觉都没有。他起初只看到来了几艘吊船,将钢索从右岸吊下来,再吊上左岸。按照这样的速度,至少也要有三年的时间才能架起这么一座桥来。这是老麻的推算,也是他的期望。不过他的期望总是落空,比如他相信“眼镜”总会坐上他的船,深入施工现场,至今他连“眼镜”的影子也没见过。而他推算的时间也出现了偏差,不是一般的偏差,是严重的偏差,不但那几根钢索在他几乎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就架设过来了(老麻曾经怀疑他们是在夜间架设的),而且桥面的木板很快就要铺设到对岸。原来他估算架桥至少需要三年时间,现在刚过半年即将大功告成。
这天,老麻独自坐在船上发呆,几滴雨水自天而降,不偏不倚地落在他的头上。雨水有些温热,像太阳能浴霸的水。老麻仰头一看,天空蔚蓝,一片云彩也没有。正思忖着,从桥面上传来哈哈大笑声,几个青年仔正在给钢索涂黄油。老麻抹了抹头上的水滴,闻到一股浓浓的尿骚味,一股悲凉顿即从心底荡漾开来。老麻双手抱头,孩儿似的呜呜大哭。当夜老麻病倒在船舱里,他被桥上那泡尿淋成重感。第三天老麻挣扎着要爬起来,老伴按住他:没人喊你“开船”了。老麻一愣,也只是愣了一下,心底像一盆熄灭了的炭火,一丝火气也没有,反而平静了。是的,码头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规矩。老麻竟然乐了,逗老伴道:你再喊一声。老伴不耐烦道:不喊了,也没人喊了。老伴几乎不到船上来,因为老麻说了,女人上船和女人下矿井都是要不得的。老麻憋足力气,伸长脖子朝着空阔的河面吼道:开船!这是老麻平生自己对自己下达的指令,是最后的呐喊,类似于溺水者绝望的求救。遗憾的是,喊声一发出即被咆哮的涛声淹没。要是往昔,这个声音就是一块巨石,会激起千层浪的。所以,眼前滚滚波涛与老麻喊声无关,他白白地喊了这一声。
铁索桥正式通行剪彩仪式,在老麻的头顶上举行。挂满彩带的铁索桥上,不时有炸响的鞭炮落下来,落到河面上,落到船头上,落在老麻的心上。老麻本来也想上岸去看看桥,他目前看到的桥是倒着的桥,没有人影的桥。他想看看正面的桥,看人走在上面的桥。为此他动员自己一个晚上,动员自己摒弃私心杂念,敞开怀抱迎接新生事物。最后他决定放弃看桥念头,立场战胜了他的好奇。老麻认为在桥头或者桥面上,他极有可能与“眼镜”相遇,这一点非常敏感,也是老麻的底线。他老麻是绝不可以在桥上与“眼镜”相遇的,他们相遇的地方只能在船上,也必须在船上。
傍午,有人从桥上伸头出来,喂了一声。老麻定神一看,是老潘。老潘说:上来呀。老麻没好气道:我不上,够兄弟你到船上来下棋。老潘说:我守桥哩。通桥后右岸供销门市部自然关停,老潘摇身一变成为守桥员,负责收取过桥费。过一趟桥收费三毛钱,收费标准和老麻一周前还收取的过渡费一样。老潘又招了招手,上来喂,到桥上来走走。这回老麻的回应斩钉截铁,不上,坚决不上,将来上了奈何桥,也不上你的铁索桥。在船上待了一辈子的老麻,原本与桥就势不两立,现在更是彻底地水火不相容了。不止桥,还有老潘,以前他们是同一个阵营,现在他投奔“敌营”去了。在旁观者来看,无论是从码头的历史沿革到时代的变迁,还是半个世纪以来老麻风雨兼程平平安安的摆渡,在码头或渡口消亡之后,守桥员都应该是老麻。尽管渡客们对老麻以往的霸道多有反感,但在安置他的态度上丝毫不夹杂着个人的情绪,他们一致认为将守桥员的位置还给老麻,是有理论依据的,因为这一位置与老麻或者老麻家族所承载的文化一脉相承。这当然是渡客们的一厢情愿,老麻肯定想都没想,何况他这样一个与桥水火不相容的人,怎么能够成为桥的守护者,不可能嘛。
老麻本来是上了岸的,上岸的时间是剪彩仪式后的第二天傍晚。这里面有个疑问,为什么通桥后第二天老麻还要到码头去?当然不是去摆渡,没有渡客可摆了,他是去收拾卧具。除了一条渡船,老麻另外还有一条卧船,是汛期夜间他值班时睡觉的船。其实每天傍晚这个时段老麻都会上岸,然而这次上岸与以往的上岸截然不同。规范的表述是,以前上岸叫收工,现在上岸叫下岗,叫失业也对,人社部门在统计就业表格的栏目上叫待业,反正都无事可干。老麻在街头“逍遥”了三天后,发现铁索桥给这条窄窄的街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前是三天一个圩日,现在天天都是圩日,每天街头都像圩日一样拥挤。拥挤的人中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连他自己也变得陌生起来。以前人们遇见他,几十米远就招呼,老大,吃了没有?现在步履匆匆的,甚至视而不见,生怕跟他招呼一声时间就哗地过去,像过去船要开动了,啰嗦一句就过不了河。第四天一早,老麻提着行李又回到码头上,并且在船上住了下来。老麻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知道如何安置自己,妥善解决自己的再就业问题。他去了一趟县城,当然是摆渡上岸的,回来后对卧船作了一番改装。卧船船体比渡船小,但轻便速度快。改装好卧船后,每天夜幕锁住河面,老麻就驶离码头。去的方向是下游,下游是顺流,到了河中间老麻就将马达关闭,任由船儿随波逐流,腾出手来操作另一套设备。清晨天蒙蒙亮,老麻准时回到码头。主顾们早已等候多时,主顾是他去县城采购设备时就联系上了。他们协助老麻从船上卸下各种河鱼,有黄蜂鱼、芝麻剑、红河鲤……也不是全部都给主顾,老麻自然要留一些的。到中午时,老伴已经在温馨的船舱里摆开了小餐桌。
几杯小酒下肚,老麻觉得这样的日子也很熨帖,这种熨帖的感觉来自船上,或者说只有船上才有这种感觉。老麻知道自己是彻底地离不开船了,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人民群众离不开码头……呵呵,码头不存在了,人民群众早已大步流星地从自己的头顶上通过。老麻像河虾一样,浸泡了酒就醉了。码头上就有一道名菜,叫醉虾。
远远地老麻就看见了老郑。老郑是乡派出所的所长,跟老麻算是老交情了。老郑身后还站着两个干警,衣服下摆露出一截乌黑的枪管。当老麻掐疼肉身,确认这不是在梦境里的时候,为时已晚,船已靠岸。两个干警跳上船来,其中一个掏出手铐“咔嚓”一声将他拷上了。老麻镇静道:兄弟,你这是……老郑也很爽快,老哥,对不起!上峰有令,兄弟我只能公事公办。
上岸时,老麻抬手示意一下,这样不大好吧,这副手表我如此一戴,戴到岸上,我这张老脸就彻底地坏完了。老郑动摇了一下。老麻说:我保证不跳河。老麻的保证是有案可查的。那一次,老郑和一名干警从右岸押着一个嫌疑人过渡,船到河中间,嫌疑人忽地跳入河中,拼命地朝原岸游去。老郑冲上船头。跃跃欲试,却不敢跳下去抓捕。老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旱鸭子。那个跳下去的干警也只会两下狗爬式,哪里追得上嫌疑人。眼看嫌疑人越游越远,老麻扑通一声跳了下去,一下子就把嫌疑人裹挟回来。在这个码头上,还没有第二个老麻这番身手。老麻不保证还好,一保证老郑就不动摇了,而是坚定了。老麻真的跳到河里去,这个码头没有哪个人可以追得回来。
在派出所里,老麻与老郑面对面坐着。老麻没少和老郑这样坐着,在船舱、在派出所饭堂,都这样坐过。老麻说:我以为你忘记我了。老郑说:哪里!我们一直都
转载请注明:http://www.hechizx.com/hcsmj/62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