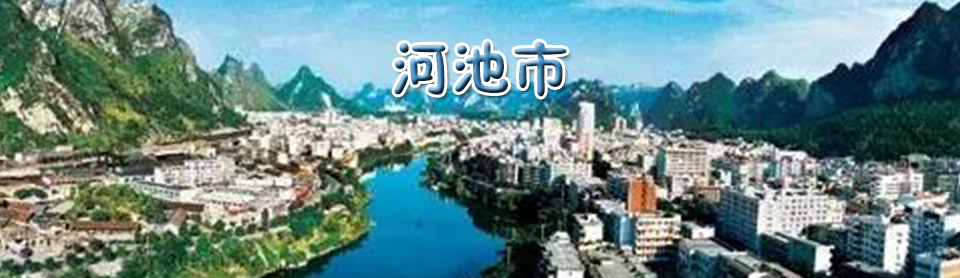张永红bull记忆中的拉平学校记
点击上方“河池文艺圈”
和万人一起品读河池看世界!
张永红,侗族,年出生,做过中学教师、新闻记者。中学时开始发表作品,有柔情散文诗系列《如果时光能倒流》《伤疼,一种怀念的方式》等在《散文诗》《青春诗歌》等杂志刊发,并入选《柔情散文诗》等集子;有童年琐忆系列散文《买书》《杀猫》《吃酒》《看戏》,以及小小说《肺结核》《那烟》《最后一户移民》等作品见诸于《广西文学》《当代广西》等报刊杂志,新闻作品《种竹种果同行》《红水河畔白鹭飞》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发,多件作品荣获全区好新闻奖。
记忆中的拉平学校
张永红
看那正茁壮成长的玉米、南瓜,还有那羞答答展开笑脸的向日葵,想那些原本开在教室墙角边点头哈腰的狗尾草,一种温暖、惆怅、淡淡的哀愁和无奈的滋味涌上心头。
——题记
七十年代的拉平,是一个有着三十余户人家的小小的屯,加上附近的上洞、下洞、垅教等几个同样的小屯,便有了六十多户人家,男女老少超过三百多人口。
有人必有学,有学必有校。
起名拉平的学校,就坐落在拉平坳上。
学校的选址、校门的朝向,都经过当时在周边比较有名望的张先生亲自踩点。左右两边是高大的青山,山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青罡、麻栗等树木,还有枇杷、李子、核桃等野生果树;前后是一片平坦的土地,视野开阔,站在操场尽头,可以望见几公里以外云雾飘渺的小村庄。四间挺宽阔的教室,还有两间专门供老师办公和休息用的瓦房。墙角遍布迎风点头哈腰的狗尾草,墙壁一律是用当地特有的青石砌成,杉木做框架,檩条上面盖着屯里群众就地取材烧制的黄泥瓦。挡风的窗子有一半是玻璃,有一半是农村劳动时用来遮风避雨的薄膜。夏天,教室里凉爽惬意,冬天,寒风呼啸着从瓦隙中吹进来,从通了眼的窗户里钻进来,奇冷,坐在里面上课,往往是手和脚都冻得麻木了。操场呈长方形,比一个标准的篮球场要大的多,黄泥填平,每逢雨天,光滑的地板会使很多孩子摔跤,屁股沾满黄泥,惹得小伙伴们哈哈大笑,只得背着书包灰溜溜的回家。每到暑假,少了人的踩踏,各种野草疯长,牵牛放马的,只要愿意在那里停上半个小时,就可以让牛马吃个饱。操场的正前方,有一张水泥板做成的乒乓球桌,球网是一块等高的木板;操场的中央,就是篮球场,球架是学校自己用杉木板做成的,装上一副用学杂费到县城买来的铁制篮圈,就是两个很标准的球栏了。课余时间,操场上可称得上热闹非凡,抢篮球投篮的,打乒乓球的,你不让我,我不服你,吵闹声一片,嬉笑声一片,有的时候,路过的家长或社会青年,也会放下锄头或背篓,拴了牛马,脱下鞋子,赤着脚,和孩子们比试几下。这山坳,倒是平添了几许生气。
记忆里,操场的左边,有一口呈正方形状的水井,深一米左右,宽不过八十厘米,上方是几株香樟树,爬满野葡萄之类的藤状植物,水从布满茂密树木的高高的石山上渗下来,除了那些可爱的小蝌蚪或水爬虫,没有任何杂物,清澈见底,冬暖夏凉,常年四季不停流淌,可以满足学校的教师和全体学生生活使用。如果长时间没有人饮用,清冽甘醇的泉水就会慢慢的沿着石板铺就的井缘流出来,沿小路形成一道小溪流。过往的行人或学校师生,口渴了,经常是用嘴直接对着漫到井口的清水喝,或是到旁边的玉米地摘下一片南瓜叶,用空心的秆伸到水里喝,或随手从旁边摘下一张树叶,卷成瓢状,舀起来喝。有的时候,那些调皮的牛或马,也会趁主人不备,偷偷把头伸到井里,快速喝上一口,不过,那大多是要接受主人的鞭子惩罚的。
在操场尽头的坎下,有两个深将近两米,宽超过十米,呈椭圆形的石灰塘,那是建学校房子的时候泥瓦匠们挖的,目的是用来浸泡石灰。虽然学校建成后不再浸泡石灰,却没有填平,常年四季,也是集满了水,那水,因为常年不能流动,久了,变成绿色,总是带着一种幽深神秘,而且经常可以看见一条条叫不出名字的蛇,在密密的水草间游来游去,无惊无惧,对我们而言,就多少显得有些恐怖。我们一般不到附近去玩,打篮球的时候,如果球不小心掉到里面,通常也是用一根长木棍把它引过来,没有人敢踩到水里去的。当然,大人们大概是不怕的,我们经常看见,如果连续几天干旱,旁边几户土地的主人,会用两只木桶,用一个带有长把的木瓢,舀那塘里的水,装满后,颤悠悠的挑到地里去淋南瓜、苦瓜或向日葵。
操场的左面,则是两个原来建房子的时候用于烧制火砖的土窑,由青石和红砖垒就,上面长满了各种小树,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在乡村路边可以随便采摘的鲜花。课余时间,我们经常会爬到窑的上面去玩耍,但是,也常常会被老师严厉吼叫制止,因为上面太危险了,一旦掉到深十多米的窑里,后果会非常严重,老师是不许我们上去玩的。
春夏交替,学校四周,那些陡峭小块的土地,都是农民们种下的玉米,有的还种着南瓜、黄瓜、四季豆之类的农作物,花开时节,学校被装扮的生机盎然,远远看去,就似一座镶嵌在鲜花丛中绿色的小城。玉米在不经意间抽穗,身上背负起一个个小小的玉米苞,我们路过时,不顾后果的随手把玉米穗子往上拔一拔,过不了多久,在炎炎烈日的烘照下,穗子就会枯萎,那一苞或两苞玉米,也便全部报废了;我们还用石头瞄准躲在瓜叶下面偷偷成长的小南瓜,看谁打的准,或是把还带着尾花的小南瓜的花去掉,过不了几天,那白白嫩嫩的小南瓜便会腐烂;有的时候,我们还悄悄溜到种有黄瓜的地里,偷偷摘下几个黄瓜,躲在高大的农作物后面,狼吞虎咽。一般来说,在乡村,口渴了吃几个黄瓜,农民大多不会放在心上,但是,有的是专门留着来年作种子的,因为老了,吃起来带着酸味,我们会把它恶作剧的摘下来后丢在一边。那时,经常有农民在被毁坏的玉米地里叫骂,经常有农民到学校老师那里去告状,经常有老师在作早操结束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庄稼,不要毁坏农民的庄稼,还常有不少同龄的孩子在放学后被老师单独留下来,写检讨,有时甚至被气愤之极的老师拉扯耳朵,打几个耳光。然而,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村民在骂完之后,从来是不会计较的,有的时候,告完状,看老师太气愤,担心老师会严厉惩罚我们,往往还要叮嘱老师:小孩子不懂事,别打骂他们,教育他们以后别再做这种事情就行了。那时,年少的我们,往往把这些伤害别人的行为当做一种游戏,所以受到责骂,也绝无悔意,倒是觉得,那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冬季一如既往来到这个小小的山村,位于山坳上的学校,就会显得更加刺骨的寒冷,课余时间,我们就爬到操场左边的石山上,用石头砌成一个个小小的火窑,捡拾随手可得的树枝或干燥牛粪,架在里面烧火取暖,有的还把从家里偷偷带来的苞谷子,或红薯、洋芋、玉米粑等,靠近火炉烧烤,然后津津有味的狼吞虎咽。那滋味,至今想起来,还是满嘴留香。
偶尔也有劳动,通常是安排在星期五的下午。中午放学,校长会集中全校学生,通知学生回家吃饱饭,几点几点,在什么地方,参加什么劳动。大多的时候,天气晴好,我们各自从家里带来锄头、泥箕等工具,统一集中到距离学校不远的地里挖泥土,然后运回学校,填平操场上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那场面倒是很热闹,挖泥的、运土的,用木板抹平压实的,你喊我应,间或还喊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之类的,一幅淳朴美丽的乡村劳作图景;有的时候,高年级的同学也会由老师带着,到距离几公里远的山坡上去侍弄学校的自留地,薅玉米、木薯,那时,我们低年级的孩子,就可以暂时放假一天或一个下午,在家协助父母干些农活,或是几个伙伴相邀到山上去放牛看马。
杀猪的日子就像过年过节。那时,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几户每所学校都自己养猪,每个学期大多养一头,也有养两头的时候,饲养员是高年级的同学轮流,轮到的要负责利用课余时间打猪菜、煮猪食,还要喂一日两餐。猪长得很快,到学期末考完试以后,学校便邀请会杀猪手艺的家长到校帮助屠杀。那样的日子老师一般不再上课,而是由我们自学。在教室里,没有了老师的管教,听到猪叫,我们是兴奋得不得了,下课铃一响,便围到操场上,看老师和帮忙的家长在忙碌屠杀和加工。下午四五点钟,整头猪被分砍成一小块一小块大概均等的肉,分给每一个学生拿回家,那些猪下水,则用一口大锅煮熟,每个学生也会分到一节猪大肠或一块猪红,用手抓着在操场上吃,那是一种多么幸福温馨而感人的场面啊……
时光留不住,三十多年过去。今天,在曾经养育了我将近十年的拉平小村,仅仅剩下三户人家,拉平学校,更是名存实亡,物是人非。其实,现在,我定居在一个叫做天峨的小城,随着交通的不断发达,有很多机会很多时间回到拉平学校,走进拉平学校。然而,每一次,开着车到达小村,站在山坳,拉平学校明明就在眼前,我却总是恍惚感到:这个名叫拉平的学校,包括那些教室和操场,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幼稚可笑的往事,都在渐渐模糊,渐渐远去,从我的眼前,从我的生命中,渐渐消失。或许,等到有一天,我将找不到回去的路,将永远回不拉平学校……
作为拉平学校的建设者,又是当时生产大队老队长的二叔说,因为拉平和周边原来居住的人家户不断迁离,适龄的学生已经没有多少,拉平学校作为一个教学点,其实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但由于客观原因,当地总有那么一些学生,无法到条件好的学校就读,所以,拉平小学,才勉强的保留下来。教书的,仍然是我读小学时就在那里的两位民办老师,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工龄,虽然政府照顾,前几年被转为公办教师,但因为年龄关系和家乡情结,不愿再到别的地方安家,也就一辈子留在了拉平学校,在拉平学校带着几个一、二年级学生,山高皇帝远,没有各种官场应酬和工作压力,倒也悠然自得,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显得那么年轻和风光;学校还是原来的学校,操场还是原来的操场,只是,原来用来支撑房屋柃条的一根被我们当作爬杆爬得光亮的粗大钢筋,已经在一夜之间不知被谁撬走,房屋年久失修,风雨稍微大一点,就会严重漏雨,所以,教室和办公室常年潮湿,打开门就能闻着一股霉味。那宿舍,摇摇欲坠的,人也就不好在里面居住,只是作为教师课间一个临时休息的场所,或堆放一些无关紧要的杂物。放学了,师生们全部离开校园,把一天的喧哗和热闹都带回家里,夕阳照耀下,那学校,便显得很是冷清、很是寂寞、很是无奈、很是萧索和荒凉。
一切似乎都已消逝,都已离我们远去,但记忆却总能使一切重现。阳光明媚,四周没有一丝风,从拉平那铺满青石的小路慢慢走向拉平学校,往事涌上心头,当年的很多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远远看去,那曾经养育过我童年的、留下我多少梦想的学校操场和教室,已是一副风烛残年、老态龙钟样子。教室旁边那块平坦却显出恬静和荒芜的土地,由于小屯外出务工的人员增多,常年没有人来耕种,遍布野草杂树,成了谁家牛马的乐园。走到近处,曾经留在记忆中的好奇和神秘,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水井和两个石灰塘都已经被泥土乱石填平,上面长满了蒲公英和肥猪菜,一条弯曲狭小的公路通过旁边,偶有一辆摩托车或拉货的皮卡车呼啸着通过,就会满天尘土飞扬,一切都没有了一点当初的痕迹,记忆中的清水和小溪流是再也看不见了;瓦窑上面已经种满了桃树和李树,季节已过,几片被虫咬得残缺凌乱的叶子微微晃动,一幅丰收过后的狼狈景象。四周的青山,则是光秃秃的一片,少了当初的碧绿与清秀,没有鸟鸣,烈日下,只看见一片片闪着白光的青石,辉煌耀眼。脚步放慢下来,思绪漫延开去,静静的,静静的,看那四周依然高耸入云的山峦,想那些原本茂密粗壮的树木,看那正茁壮成长的玉米、南瓜,还有那羞答答展开笑脸的向日葵,想那些原本开在教室墙角边点头哈腰的狗尾草,一种温暖、惆怅、淡淡的哀愁和无奈的滋味涌上心头……
编辑:审国颂陈昌恒
往期精彩回顾石才夫?诗意四月天,读一本《流水笺》
翔虹?大小天峨
故园春色——韦俊平三月水彩新作
红日?最新短篇力作《暗香》
黄伟?坚定文化自信,助推脱贫攻坚
潘莹宇?穿越从林上大道
陈昌恒?蜿蜒在山路上的黄金岁月
韦东柳?山城东兰
罗雯?印象高岭酸
莫梦霄?没有负重前行,哪得岁月静好
当瑶妹遇上满河花开,怎一个美字了得
黄格?远是风景近乃人生
疫情过后,邀你一起看遍大美罗城
从此“疫”后,让我们珍惜这些美丽和幸福
唐青麟?在都安的天空下
从都安到宜州,乡音不改,永是故乡人
韦强?“防控疫情,万众一心”主题书法作品展示
翔虹用心讲述韦波深情演绎,一个天峨女孩的温暖故事
韦于婷?我的那些花儿
荷塘花开又逢君,河池这地方美翻了
凝望?河池机场,一个吃住行乐无忧之地
审国颂?愿你历尽沧桑依然坚守善良
河池文艺圈
我为家乡代言
河池文艺圈主编审国颂
不是每个人都是作家
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如果愿意
我在这里等候分享你的故事
河池文艺圈投稿须知1.文体不限,讲述河池人河池故事展现河池风光及民族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含散文、诗歌、小说、书法、美术、摄影、音乐、在校学生习作等)优先发表,字数控制在字以内,摄影组图一般不少于10张。
2.来稿请附作者简介、联系方式和个人照片一张或两张,文章如与内容相符的插图的可一并打包发送,由编辑选发。
3.作品为原创的,本
转载请注明:http://www.hechizx.com/hcsxw/74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