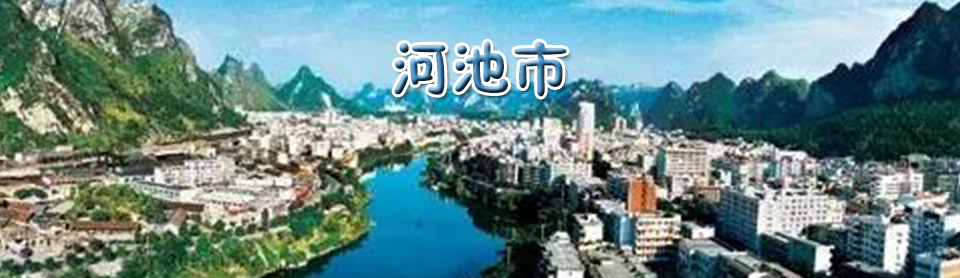散文蓝宇关于五张图片的说明
作者简介
蓝宇,瑶族,年生,大化贡川人,广西作协会员。有散文、诗歌作品发表于《三月三》《民族文学》等。好诗书,喜耕作,聊有空闲,饮酒种花。
关于五张图片的说明
文/蓝宇
图一龙那肯学山老宅
关于童年,大概有一半的记忆是印刻在这半座山头上。图中所示1原是我爷爷家,不过从记事起,我爷爷已经不住这里了。我父亲几兄弟相继成家后,那两间茅草房分给了我四叔,所以那里就成了四叔的家。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山上,也就是图中所示4处。我小时候,不是在4处的茅檐下捏泥巴,就是在2处的榕树下拣榕果,在北坡的枫叶下守望从田里归来的母亲,从讲堂上下课回家的父亲。
2处往左去,就是我曾在《从北坡到乡关的守望》里写过的北坡。北坡有一片枫树林,初春绿茸茸的枫叶从枝头钻出来时,母亲就要随打工大军走过长长的吊桥山,出去打工去。那时候我父亲还在隔壁屯当教师,所以我每天除了跟父亲去学校,剩余的时间就是在北坡张望。关于2处的大榕树,其实还是有一些故事可讲的。首先是关于榕树根下的树洞的故事。据说那是祖奶还健在时,叔伯还小的时候。
我们山里人喂养婴儿的食具,是一个长鼻的陶罐煲。每天用敞口锅煮好一大锅倒影茅梁的玉米糊后,家里有婴儿的人家会从木缸底抓一把大米放进陶罐煲,倒入许些水,割一块已带腐味的腌肥猪肉,将灶里的火灰巴拉开来,将装着大米和腌猪肉的陶罐煲放进火灰推里慢慢煨熟。等大人喝饱了一肚子玉米糊浆,陶罐煲里的腌猪肉香便飘满茅檐下的一方矮房。女人搬来矮凳,从襁褓里剥出婴儿,用一个瓷勺挖一口米饭咬一丁肥腌猪肉,自己嚼碎后又吐出来喂给婴儿。那腌猪肉的香味和大米的甘甜,只是在她们嘴里短暂过了个味,便被无余地吐出来,送到嗷嗷待哺的婴儿嘴中。
能吃上陶罐煲饭,是童年里每个儿童最高的待遇,即使只是大米饭,没有腐味的腌猪肉。因这缘故,小孩子有事没事总是盯着陶罐煲看。说是一天午后,兴许是馋坏了的祖奶偷偷煲了陶罐煲饭,想给自己解解馋。谁知陶罐煲饭的香味实在太过于稀有,以至于已经跑到山脚去游荡玩耍的叔伯们嗅味而归。
首先到来的是父亲和大伯,他们一个老大一个老二,仗着自己多喝了几年奶水气力足脚程好,一骨碌跑进茅檐下爬到灶台边,趁着他们奶奶我祖奶不注意的空档,两人心领神会拿起滚烫的陶罐煲就往北坡跑去。到了大榕树下,瞧见大榕树根下的树洞,两人十分默契地端着陶罐煲就钻进树洞里,开始了他们大快朵颐的抢食行动。
可惜的是,陶罐煲实在太小,而大伯和父亲心又太急,两个人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争先恐后将小手伸进陶罐煲里,两只小手因紧抓米饭而被窄小的陶罐煲口卡住,二人同时使力往外抽出手时,竟将陶罐煲挣破为二了。
这两兄弟倒也心大,索性你一半我一半各自捧着半边陶罐煲吃起煲饭来,全然忘记了这是家里唯一的陶罐煲,是大人当了宝贝一样看待的东西。
等他们吃净了各自手里的半捧陶罐煲饭,剩下几个弟妹终于气喘吁吁跑来了。他们嗅着残余的香味爬到榕树洞口,看着自己大哥二哥手里被舔得光溜溜的两半陶罐煲,一个个既伤心又难过地哇哇大哭起来。因为,他们错过了一顿美味的陶罐煲饭。即使,那只是一口两口的量,他们依旧觉得自己错过了绝世的美味。
他们的哭声很快引来了他们的奶奶我的祖奶。结果可想而知,这两兄弟免不得祖奶一顿好打。然后那个凶巴巴的我的爷爷回来之后,接力一般接过祖奶手中的棍子,又将这两兄弟一顿打。
不过第二天后,他们兄弟两就忘记了昨日里自己屁股上挨的那些棍子了。他们开始满脸得意地向几个弟妹宣讲陶罐煲饭的美味。至于棍子打在屁股瓜上的疼痛,于他们来说倒如风一般过便无影无踪。
小时候我在四叔家篱笆院的石墙上见过那个被大伯和父亲分为两半的陶罐煲。它和石墙上的石头一样,已经布满了青苔和污垢。后来四叔搬下山脚后,无人维护的石墙被大雨冲毁,那两半陶罐煲也就埋入了地底,像当年将它珍视的那几个老人一样,回归了铸就他们的泥土地。
除了这故事,大榕树下让我挂心的,就是已故的五叔的茅庐。
五叔的茅庐在大榕树底偏上的一块巨石下,那是他嫌弃爷爷吵吵他看书后自己动手搭建的一间离群索居的小茅屋。茅屋仅有一床大小,就搭在一棵歪脖子李树下。
五叔是几位叔伯中读书最狠的,因为穷,他读到大学时在一次暑假打工中意外身亡,他的小茅庐也就被弃之于半山腰的凄风苦雨之中,日渐凋败腐坏,如他的无了灵魂的皮囊,消融于那一片山水间。
我读到小学二年级后就离开了山屯,但每一次回乡,我总要到大榕树下去转转,去看一眼五叔的茅庐旧址。
我记不清那是经历了多少年风雨侵蚀的茅庐,在我的印象里,我看到它的最完整的模样,是几根腐朽的烂木头斜斜垮垮耷拉在歪脖子李子树的树杈上。倒是平整不减分毫的青石板到如今还依旧沉默着留守在那一块故地,固执地向我这个有心人证实着曾有人在这里住过。
对于五叔的记忆,就如对于烂茅庐的印象一样残破不堪。我有时甚至怀疑在我童年里是否真有那么一个叫作五叔亲人,曾经背着睡在襁褓里的我走过北坡的枫树底,到北坡最北边的那块山石上,远眺山外蔚蓝的天空。可是屯口那一方矮矮的坟墓,和半山腰榕树底那一片平整的青石板,赤裸裸地告诉我那个人确实来过这个世界。
这是埋藏在大榕树底的人和事,曾像山风一样刮过那片葱郁山腰,然后爬过北坡的山石,逃开去了。
看图3所示,那是一个长长的土斜坡,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里用砍来的树枝当马车,一帮人在上边坐,一帮人拉着树枝往斜坡下疯跑,乐此而不知疲倦。
斜坡到顶,有一片颇为开阔的开荒地,那是母亲开荒出来种芋头的泥土地。芋头地的地垄边有一棵棵高矮不一的梧桐树,每当母亲在芋地里培土除草时,我就在蹲在地垄边上的梧桐树荫里,抓一只蚱蜢将整窝的蚂蚁诱出来,看它们将大于自己百倍的蚱蜢拖到窝洞口,却再也无法把蚱蜢拖进窄小的洞里去。秋末冬初,满树的桐果压弯树枝的时候,我又和母亲背了箩筐,在呼呼吹过的山风里采摘桐果。
图4是我出生的老宅,那是我伯爷留给我父亲的遗产,作为父亲给他送终守孝的馈赠。
老宅是两间不大的茅屋,屋后有一排桃树,春天一到,春雨飘洒,桃花便随春风飘飘摇摇荡了起来,和朦胧春雨一起营造出茅屋前后的一点仙境气息。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发在河池日报的副刊上,说的就是童年时在这里的生活模样。
图5处有一汪三四平米的小池子,狭长浅显,虽常年储水,却只是垫底的那种。
我曾趁着三叔外出的空档,偷偷跑到山脚处他开挖的鱼塘里,一口气抓了十几只塘角鱼到小池子里放养。那晚外出的三叔回来后发现鱼塘浑浊不堪,知道定是我捣的鬼,提着棍子满村子想要揍我。
那时候我就躲在山腰上的小池子里,听着山脚下三叔的骂声如雷奔上山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好在那晚已经到邕工作的父亲破天荒回家来,三叔看在他的面子上,不好意思再找我麻烦,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直到一年后,我从小池子里抓起仅剩的几条塘角鱼,已经长到半斤重的鱼儿让我和两个堂弟堂妹在四叔家美美喝饱了一餐鱼汤。
还值得一说的就是小池子边上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夏天时我们最喜欢躲在如盖的树底下乘凉,玩石骰子,捏泥巴,遥望着达边姑娘的家门,隔空跟腿脚不便的她逗趣。我曾用两千字的篇幅让那个苦命的姑娘活在我的文字里,和茅檐下的文字一样,刊在河池日报的副刊上。这得多谢那位编辑,让达边这个姑娘被更多的人们知道。即使她只如风拂过。
可以说,这张图一囊括了我童年一半的记忆。那些记忆里的一草一木,如今在图里已经零零星星参差不齐。像极了曾经生活在图里世界的人们,失落,遗失,在奔流不息的时光洪流之中。
图二龙那肯学山脉
图二是肯学山山顶的模样。如图所示,1处曾经在我的文中出现过,这个地方有个近似乎响亮的名字,因为它的名字和《水浒传》里的景阳冈只差了一个字,就叫景岗。只不过景阳冈因老虎和武松而闻名,而景岗却因魅婆的传说而被屯里人所熟知。
其实景字在我们当地的语言中是鬼的意思,所以景岗的确实意义就是鬼岗。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为鬼岗?我曾在《重寻那山那水那时光》里有过描述,这里就不再作长篇赘言。简而言之,这里是对面山洞中魅婆落脚的地方,凡所在此逗留的人,都会遇上一些诡异的事情。
下来图2中,我在以前的文中也有所提到,这里生长着几棵茂盛的树莓,所以虽然离得景岗很近,但我们在树莓成熟的季节还是会组队去采摘树莓。图3处的山顶有一个石垒的小堡垒,老人传言是剿匪时解放军所筑。但根据精于历史考据的覃校长推断,此处堡垒应为太平天国时期的产物,非剿匪战争时期。至于到底为何时之物,有待进一步考究。
图中箭头所示,为相连的另一座山头。其上也有一个石垒的堡垒,和图3所示为同一时期产物。小时候我们曾经多次爬到山顶去寻访历史足迹,寻找从解放军的驳壳枪里打落的弹壳。可惜,除了一块块石头,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记得那时候爬这座山时,有几次我是光着脚去的。山顶嶙峋尖锐的石崖让我记忆犹新。
图4中我从去过几次,至于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好像是跟堂姑去放羊还是放牛啦。不过,那个地方可以清楚看到隔壁屯的全貌,有一条悬崖小路穿过刺槐丛通向山背,这个场景曾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像是一条通天之路一般神秘幽幽。
图三龙排屯全貌
图三1处是龙排屯的水池和鱼塘,图2是我的母校龙排小学。之所以将学校标在水池和鱼塘之后,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远比学校更加吸引着我。我在这里读小学那会,没少在这里偷偷游泳,钓小鱼小虾。
这里给我的记忆除了游泳和钓鱼钓虾的乐趣外,可能使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某次游泳时,一个大年级的学生坐在水中一根浮木上,将我的脑袋硬生生往水里摁,以至于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掉了。
图2处的记忆,有些复杂。总之,在学校里我是好事做过,坏事也做过。优秀学生当过,坏学生也当过。偷过同学的作文簿,拿过老师的水笔,还在高年级的教室外吆喝过“收蛤蟆啦,我家收蛤蟆啦”。我在这里偷偷喜欢过某个小姑娘,也在这里和班里的某些男同学干过架。在泥球场上踢过球,脚指甲在硬石块上开过花,也曾光着脚满屯子疯跑。那都是在学校里满满的回忆。
图3就有些不好玩了。因为这个地方是一片坟场,就在我们学校的后面。不过,好坏参半。这里虽然有让我们心生恐惧的累累矮坟,但坟场边有一棵大树,大树到了四月,会长出辣椒一样的嫩树叶,酸涩酸涩的,想起来就让人流口水。
那时候我们一下课就跑去大树下,用棍子打下大树辣椒一样的嫩树叶,沾着粗盐吃。吃得一肚子酸水,吃得肚子咕咕叫。但是我们还是爱吃,越吃越饿,越饿越吃。
我的一篇恐怖小说《红荔枝》就是根据流传在屯子里的鬼怪故事写就的,故事里的场景,就是以此地为背景而展开。而小说中那棵荔枝树,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那棵荔枝树就在1处过去不远,树干有三人合抱之围,高达十余米。荔枝树下也是个矮坟扎堆的地方,爷爷还在世时没少跟我说过那方土地上的鬼故事。
图4是一片茂密的树林,里边有一种珍贵的树木,我们叫之为金刚木。这种树非常坚硬,是制作陀螺的最佳选择。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偷偷跑到山上砍木头,为此没少挨过大人追骂。树林里到了秋天会落下一种如佛珠一样的果子,我们常常是下午的晚读时间,偷偷翻墙跑出学校,从屯子里的篱笆院,像做贼一样低俯着身子摸上林子里去捡那些果子,回家后用针线串起来,做成一串串佛珠子。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坚果的一种,类似于某种野生的板栗。
箭头所示,是通向一个叫做弄水的垌场。因为我们祖奶曾经葬在弄水一个山泉边,所以我对弄水还是有一些好印象。通向弄水的山路是一条笔直的石板路,那石板路干净光洁,像极了我们屯通向山外的吊桥路。
图四龙那、龙三屯
图四中1处原有两棵榕树,以前每年到了掰玉米棒子的时候,从地里挑两筐玉米棒子到了该坳口,无论大人小孩都会撂下担子,在榕树下的石板上坐一坐,歇一歇脚。两年前修建公路,两棵长势极好的榕树被无情地挖掉了。
在榕树两边,是依山而建的一条百十米长的城墙。是旧时为防御匪寇劫屯而建的,到了夜晚,城墙上有成年男人持枪守夜,防止匪寇趁夜来袭,打家劫舍,祸害妇女。
这条见证山屯历史变迁的城墙,因为修建公路缺需砂石的缘故,被外来的势利眼承包商全部拆除,丢进打砂机里轰隆隆碾成了砂子。这样,山屯的历史见证人就一文不值地被人们踩到了脚下。人们终于还是忘记了,曾是脚下的它们,为人们挡住了匪寇的一次又一次来袭。
图2处是一片林子,和图三那一片林子一样,也是我们曾偷偷跑进里边砍树的地方,只为做一个又大又圆的陀螺,好将别人的小陀螺杠飞。图3处是屯子靠山上一块藏地,多有坟穴,也是牧场。据说阴天雨天时常闹鬼,小孩少有人去。只是在捻果成熟的季节,一群孩子才在大人的牵引下上去摘捻果。
图4处是我大伯家,也是我们蓝家到龙那屯落户时第一块老宅地。因大伯搬迁贡川凤凰,前不久他在这里辛辛苦苦建起来的一层两间平房被挖掘机两铲子夷为平地了。除了酒缸,大伯对于一众家具未取一样,全让它们连同房子一同藏灭了。问他何故,答曰:房子那么好我都不要了,还在乎那几件破烂家具?我只有呵呵作态,不做评论。
图5处是我外婆家,小时候第一次喝酒醉就是在这里,被几个舅舅骗的。箭头所示是通向弄塌的横山路,这条横山路在我看来是一条颇有意境的山路。因其蜿蜒穿山而过,路边林深树茂,脚下石道光溜,沿途一味幽深清净,颇有曲径通幽处的妙趣。
故此有时回去,我会一个人去走一走,领略一番清净妙趣,顺便沿着山道前去,到那尽头处去看一眼让我心生悲凉的弄塌。
弄塌是个颇大的垌场,小时候跟母亲下地,大多的回忆是在这个地方。记忆里总是记得冬天时候,和母亲去地里锄荒,天至黄昏时候,北风萧萧刮过山岗,半空里荒烟袅袅四起,而满山满山的白色荻芦摇摇荡荡,山林间寒鸦凄切,百草枯黄,让人心生悲凉,不忍卒望。
那是一个,让我小小的心灵第一次体会到天地苍凉与辽阔的地方。
图五龙那屯(半景)
这是龙那屯一半的景致。图1处是我们屯中央的老粮仓,两间颇为宽敞的瓦房。赚公分过活的年代,这里就是屯里存粮放食的地方。我记事起,这里已经失去粮仓的作用,只作为屯里每年腊月整屯驱邪时的聚餐之地。
粮仓外有一片空地,旧时是粮仓的晒谷场,粮仓“倒闭”后,空地成了孩童的游乐场。放学后,孩童们就在这里赛陀螺,打尺,玩游戏。直到天黑后才被各家大人喊回家去。这片空地在夜幕降临之后成了青年男女对唱山歌、谈情说爱的场所。
图处2是一片洼地,之所以标出,因为这里的罗姓人家的小姑娘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惜长大后远嫁到了四川某地,音讯全无。这里有多棵龙眼树,是一个乘凉纳阴的好地方,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耍之地。
图4处就有些故事了。这里住着一个我喜欢了很久的一个姑娘,我曾为她偷偷写情书,甚至还为她学会写情诗,可所谓是她开启了我最起初的文学之路。
所以,我怀念这个地方。
不过话说回来,至今为止,我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哪怕是到近前看一眼。我曾远远地偷偷注视这个地方千百次,但我还是没有勇气踏足那一片心中认为神圣无比的土地。我记得那个地方有一对白鹅,每次白鹅曲项向天歌时,我准就能看到那个姑娘挑着一副水桶晃着一头长发下山来挑水的欢快模样。
那些藏在心里的秘密,美好而遥远,铺满在闪着星星的小屯夜空之下。所以,所有的心事便如一汪凉水,倒影着那些闪亮的影儿,却怎么也触碰不得。
这便是遗落在山间屯里的些许往事。随着这五张照片的定格,一幅幅记忆画面从图中悠悠铺现,一个个远去的身影,从心底含笑走来。
监审:覃继虎
编辑:韦承松
阅读推荐
今日头条|河池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在金城江开幕杨龙文蓝胜姚本喜率大化代表团出席
今日头条|自治区主席陈武深入大化检查脱贫攻坚工作
今日头条|筑就“民心路”打通乡村脱贫动脉
今日头条|大化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县域经济活力
今日头条|大化:把您的夜晚让我安排把我的夜晚与您分享
今日头条|杨龙文在雅龙调研时强调敢于担当履职尽责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今日头条|越夜越红火越夜越精彩大化打造“大都马”夜经济新地标
今日头条|杨龙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
宣传推介大化传播最新要闻
大化视点是中共大化县委宣传部打造的集时政发布、宣传推介、便民服务为一体的官方网络新媒体平台。凡转载本
转载请注明:http://www.hechizx.com/hcstc/62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