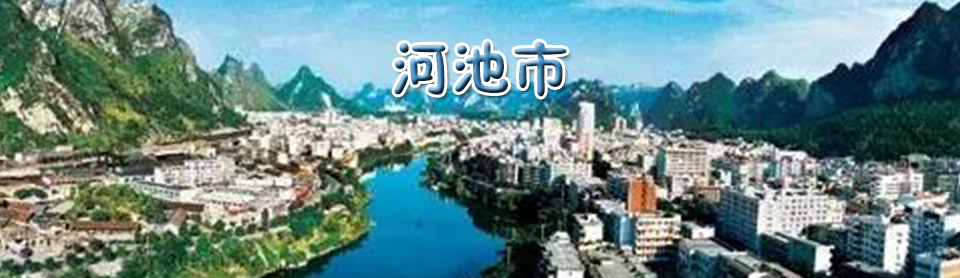蓝安光bull亦兄亦父恩难酬记忆
点击上方“河池文艺圈”
和万人一起品读河池看世界!
蓝安光,广西都安百旺人,瑶族,大学学历,曾在都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大兴乡党委、都安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现供职于都安县二轻联社。
亦兄亦父恩难酬
文字
蓝安光插图
韦俊平
二O一八年五月十七日早晨,我还没起床就接到嫂子的电话,她说:“黎城爸,不知什么的,你哥说不了话啦,赶快过来。”
我二话没说,驾车直奔哥家。当我赶到时,哥已经走了,他的时间定格在那天早晨的6点20分,享阳66岁。顿时,我泪如雨下。
我的祖辈是在百旺仁合一个叫弄核的山?里。一九六五年的一个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祖房给烧光了。后来听说是因为我父亲养的猪满栏,羊满山,鸡满笼,客人来了不是杀鸡就是宰羊,有人嫉妒,便趁着黑夜一把火把我们的房子给烧了。但我相信,那仅是传说而已。
祖房没了就得重建。在重建问题上,父亲与母亲意见不一,父亲舍不得兄弟,坚持在原地建,而母亲想要搬到山下建。最终父亲拗不过母亲,同意往山下搬迁。
当年爷爷是有远见的,他勤劳能干,手头有些积蓄。父亲出生后,爷爷就筹钱在山下巴广屯的巴广山一带买了十几亩的荒地。当时地价便宜,爷爷用几斗米、几斗黑豆、几头猪仔就买下了那片地。因为有了这十几亩地,母亲才坚定往山下搬迁的决心。
听奶奶讲,父母为建新房不分昼夜地在老家的自留山上砍树做横条,还找工程队舂墙。当时没有水泥砖,起的都是泥瓦房。所谓的工程队,其实是几个舂墙能手,包括我的叔叔蓝萃锋、蓝启培、唐钟川、唐爱琮、唐钟才、爸生、覃继禄(后改为韦振禄)等。父母常常是白天与大家一起舂墙,晚上就到弄核的自留山砍树,奶奶在新房的工棚下带我们五个孙仔——大哥,三个姐姐和我。
大姐蓝美杰是我爸从隔壁菁盛乡新城村提多屯里一个亲戚那里抱养的。大姐虽是养姐,但我们一直把她当作亲姐看待。据奶奶说,我父母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爷爷和奶奶心里直着急,后来有“高人”指点说我父母命中缺“引仔”,只有抱养一个孩子,才能有自己的孩子。为此,爷爷奶奶四处打听,得知菁盛新城一远房亲戚家里很穷,家有五个男仔两个妹仔。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作怪,加上两个妹仔体弱多病,正想找人抱养。爷爷还亲自上门为抱养说情,亲戚答应了。爷爷把美杰姐背回家时她已两岁多,但身瘦如柴,体重才有五斤。美杰姐到我家的第二年,她的妹妹在老家夭折了。美杰姐在爷爷、奶奶和我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后来嫁给仁合村那好队我的姐夫覃继寒。说来也怪,还真应了“高人”的话,美杰姐到我家后的第二年,我们四兄妹相继出生了。因此,我们一家人都发自内心地爱着大姐,待她比亲姐还亲。
一九七O年,我5岁。那年除夕,于我家而言,那是永生难忘的日子,我们亲爱的母亲,那一天离我们而去。
那天,父亲强忍悲痛让我们与其他家庭一样杀鸡过年。我记得父亲对哥说:“平,虽然你母亲过世了,但你奶奶、妹妹、弟弟还是要过年啊!你把那只线鸡拿来杀,今晚我们就在你母亲的棺材旁过年。”当时,我倚在奶奶的怀里,因为年纪太小了,不知失母之痛,照样活蹦乱跳。
母亲是患肝硬化腹水而死的。她病的时候,因为我和两个姐姐都还小,据哥哥后来跟我们说,为了治母亲的病,他曾多次下忻城、上拉烈、跑菁盛等地方找土医。有一次,听说忻城县某地有位中医能治母亲的病,父亲就叫哥到忻城找人取药。说起去忻城,对于现在来说,这不过是两小时的车程,但对于上世纪70年代来说,可要走一天的时间。哥哥一边问路,一路小跑,找到那位中医时已是下午五点了。拿到药之后又一路小跑回家,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当父亲给母亲熬药时,母亲说爱吃鸡肉。没办法,家里再也没有可杀的鸡了,几个月前就连老母鸡也杀给母亲吃了。于是父亲又叫哥哥到我们的老家(弄核队)买鸡,买到鸡时已到凌晨一点了。哥哥点着火把,提着鸡沿着山路一拐一拐的往家的方向走,奶奶看见火把时,不停地喊:“平,你慢点,我看见你了。”到家之后,哥哥也没能歇歇一下,他还得杀鸡弄给母亲吃。哥哥把整只鸡煮给母亲一个人吃,刚吃完,母亲又说还想吃。母亲的这一情形让我们一直担心,我们不知道这是病魔作怪还是老人常说的回光返照。没有办法,哥哥只好又杀了第二只。母亲就是这样折腾平光哥。
在我的印象中,我只隐隐约约记得母亲的脸面。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带母亲到拉烈公社(现为拉烈镇)卫生院看病,我也闹着要一起去,没有办法,父亲只好答应了。当时父亲是用马车拉着母亲去拉烈卫生院的,那时在乡下是没有救护车的,客车都很少见。父亲赶着马车,我靠在母亲的怀抱坐在马车上。我依稀还记得,母亲的肚子很大很涨很鼓,像个大南瓜。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才到拉烈卫生院。经过医生检查,确定母亲的病已是肝癌晚期,没有再住院治疗的必要。为了减少母亲的痛苦,医生还是给母亲插上导管,把肚子里的水抽了出来。因为是肝硬化腹水,医生足足抽了两个多小时,两提桶水装得满满的。抽完水之后,母亲没那么难受了,脸上又挂起久违的笑容,我们又坐上马车回家了。
经过一年多的医治,母亲的病最终还是没能医好。
母亲去世后,一家人的负担就全落在父亲的肩头,父亲明显地憔悴了许多。在母亲过世一年后,为了找个帮手分担养家的重任,父亲娶了后母,不久还生下了我的妹妹蓝雪莲。
后母的到来,让我们的家庭增添了一些温馨,让我们兄弟姐妹觉得这个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七四年临近端午节时,父亲因突发心梗(当时壮话叫做发“丹鹅”)又离开了我们。父亲过世后不到半年,后母承受不起重担,带着妹妹蓝雪莲转嫁百旺崇文村。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那年刚满十七岁的哥哥就得当家了,尽管当时哥哥连家都还没有成。
父亲也是个有打算的人,还在世时,为了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他操透了心。尤其是哥哥日益年长,要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了,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委托媒人蓝光增到河怀屯的李维京家打探,其实是想要李维京的妹妹李爱珍做我的嫂子。
说起提亲这事,还有一个小插曲。
上世纪七十年代提亲比较简单,一壶土酒,斤把肉,一两包青竹香烟就可以到女方家去说亲了。只要媒人和女方家说通了,这门亲事就算成功了,出嫁的女人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就是挨嫁,沿承了封建的包办婚姻这一陋习。
去给哥提亲时,父亲准备了一刀腊肉、一壶酒等给媒人蓝光增带着去。父亲嫌腊肉太长(因为那年我家杀了有史以来全村最大的猪,多斤),把腊肉割成三节,然后用旧报纸包好。父亲的这一操作到了李维京家,人家理解可不一样,认为父亲太吝啬,腊肉都不舍得拿成块来,还割一半留在家里。为此,李维京家起初耿耿于怀,还好经过蓝光增那三寸不烂之舌说明了原因,最后还是同意把妹妹李爱珍嫁给哥哥。
哥哥的婚事是在父亲过世后才办的,非常简单。婚礼当天,家里摆了三桌酒席,来的客人主要是同祖宗的亲戚,本屯各户一家一人。李维京为妹妹准备了两个木箱,算是陪嫁礼物,木箱里有几件新衣服,一床棉被,一床蚊帐、脸盆、口盅、茶筒(热水瓶)等等。哥哥就这样没有一声鞭炮、没有花车,连“三转一响”都没有一件就完成了婚事。
爱珍嫂子的到来,注定要过漫长而艰苦的生活,一方面要负责扶养我们姐弟三个和八十多岁的奶奶,另一方面,还要和哥哥生儿育女。
爱珍嫂嫁到我家时,当时还是生产队统一劳动,按劳取酬,挣工分是头等大事。记得当时不管嫂子如何努力起早贪黑地劳动,但一年到头,还是超支。因为那时家里只有哥和嫂是劳动力,全家七八口人吃饭,我们姐弟三个还要读书,加上婚后不久,哥嫂的三个孩子陆续出生,都还小,奶奶又上了年纪,全家就靠哥嫂两人挣工分,不超支才怪!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二姐蓝美利读到小学二年级时不得不选择了辍学,早早地加入了生产队的劳动队伍,和哥嫂一起挣工分养家。二姐本是个爱学习且记性好的人,在学校读书时她在同龄的女生当中是佼佼者。我至今还记得她强忍泪水离开学校的情形,也一直铭记至今,假如当初没有她的这一选择,也不会有我和三姐后半生的好生活。
平光哥哥是文革时期的老高中。在巴广屯,文革时期的高中生没有多少个,哥算是个有文化的人。那个年代有文化的人是很受社会尊重的,哥哥后来也因为这一点,命运转了个弯。当时学校正好缺老师,哥哥被聘用到百旺的仁合小学当代课老师。这是我们这个孤儿家庭里的第一个领工资的人。当时哥一个的月工资是18元。18元在七十年代是很顶用的,当年的鸡蛋一个八分钱,一碗粉一毛二分钱,猪肉是七毛六分钱一斤,一对香蕉五分钱。哥哥靠着这18块钱的工资,填补了家中的空缺,从此,我们能过上逢年过节有肉吃的日子。
哥哥当代课老师的第二年,时任百旺公社书记的韦元寿发现了哥哥是个能说会道,又能写一手好文章的青年,是培养行政干部的好苗子,于是吸收哥哥到仁合大队当文书。当年公社书记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说要谁当什么就要谁当什么,没有人反对的,更何况当时有文化的人又少。那年,百旺公社需要配给仁合大队一位能做能说能写的文书,哥自然是不二人选了。
哥当了大队文书,这是件好事,可这一来可辛苦了爱珍嫂,犁田耙地、砍树挑粪、扛打谷机等这些本应由男人来做的工作从此全落到嫂子一个人的身上。爱珍嫂每天依然不分昼夜地劳动,白天一刻不落地参加生产队劳动,放工后,还要砍一担柴火回家,到家之后还要去挑一两担水,还要哺养嗷嗷待哺的孩子,打理家中的猪鸡鸭牛羊。每天忙完这些已经将近晚上的十二点了。尽管如此,爱珍嫂从不埋怨,她常对哥说:“你是国家的人,家里面有我,你就安心工作吧!”
哥哥对待工作是极为认真负责的。常言说“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哥哥的工作人民群众是看得见的,领导是记在心上。一九七四年七月,上级有政策,吸收部分大队干部为国家干部,这对于我哥哥来说,是一件大好事,经过层层考核、政审,仁合大队破天荒地有三名年轻大队干部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个。
成为国家干部之后,哥哥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和几个刚被吸收为国家干部的年轻同志一起,到都安最远最偏僻的乡镇——大化公社景山大队当三分之一工作队。这一工作队一当就是两年,哥哥与几位年轻干部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与景山大队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二OO六年,我在都安百才新区起自己的新房。为了搞一楼的水磨,我找来做水磨的师傅,很巧,当时在都安县城搞水磨工程都是大化人。当我和师傅说起当年我哥哥也曾在大化当三分之一工作队时,师傅不约而同地问,是不是叫做蓝平光?师傅们还说他当年如何如何努力工作,如何如何体贴群众,如何如何能干。我立即给哥打了电话。那一晚,我、哥哥和师傅们聊得可欢了,喝得可甜了,推杯换盏间,大家把在大化公社景山大队工作的经历如数家珍还原了一番,仿佛那些事昨天刚刚发生,说到激动时,哥热泪盈眶。
哥哥在大化公社当三分之一工作队这两年,还是辛苦了爱珍嫂。她一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一边要操持全家的大事小事。那时我和两个姐姐都还小,哥的三个孩子最大的蓝艳红也才六岁,最小的蓝黎明刚一岁多。还好奶奶还在,三个小孩就一直由奶奶带着。除了带孩子,奶奶还得煮饭、喂猪,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做事并不比年轻人做的事少,除了干家务活,带曾孙,她还经常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劳作呢,除草、捡猪菜、割羊草,给玉米施肥,种黄豆,种花生,哪样都没落下。若是没有奶奶分担,真不知道嫂子该怎么过来。父亲是奶奶的独苗,父亲过世得早,白发人送黑发人,奶奶内心的伤痛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还好有“二男四女”的孙辈,在奶奶心里,这个家总算还有希望,也正因为这样,奶奶努力的发挥着她的余热,和爱珍嫂一起养护着这个家。
平光哥两年的大化公社景山大队知青生活转眼就过去了。由于哥的表现好,组织把他重新分配到百旺公社担任组织委员。到了百旺公社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一周能见上几次面。哥哥就近工作,多少也能分担嫂子一些家务事,至少有个什么事了多了个人可以商量。哥到公社工作后,家里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每周可以吃上肉,身上衣服每年可以添件把新的。村上的人对我们这个曾经濒临破碎的孤儿家庭也另眼看待。
后来,我们姐弟三人渐渐长大,二姐到了谈婚论嫁年龄,嫁到八甫村盘龙队蓝冠业家,三姐蓝美良读高中,我上了初中。哥哥的三个孩子也逐渐长大,蓝艳红、蓝艳玲、蓝黎明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一家五个人读书,在我们巴广队的历史上是很少有的,高中、初中、小学都有我的家人在读书,这或多或少增加哥嫂的负担,但他俩从无怨言。哥嫂常对我们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读书才能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片立足之地。也正是这一理念支撑着他们,也支撑着我们,一直到现在。
可哥哥最终还是抛下我们走了。走时一声不吭,沉默得像一块石头。
如今,这块石头沉睡了整整两年,任凭妻儿和兄弟姐妹怎样撕心裂肺地呼喊,最终没有醒来,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没有一丝模糊。
编辑:审国颂陈昌恒
“我的青春我的芳华”
主题征文活动开始啦!
本次征文活动,旨在给每个有故事的你一个平台,用心情做笔,以岁月为纸,用文字书写青春,讲述经历,记录梦想,传递青春正能量。
韦德乔审国颂覃振江黄玉兰
张天德陈昌恒潘丹妮黄伟宁
河池文艺圈红水河文艺在线
年5月1日至6月15日
题目自拟,要求贴近主题“我的青春我的芳华”,内容励志,真情实感,积极向上,文体以散文、散文诗、现代诗为主。散文字数不超过0字/篇,散文诗不超过字/章,现代诗不超过30行/首。作品附作者照片、联系方式、百字以内作者简介。
qq.转载请注明:http://www.hechizx.com/hcszz/6283.html